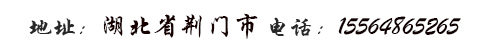稷下问学叶诚生朝花夕拾中的儿童叙
|
作者简介 叶诚生,年生,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年)。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著有《现代叙事与文学想象》《鲁迅的诗歌艺术》等,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 摘要:儿童叙事作为鲁迅创作伊始既已使用且在日后写作中不断实践的一种修辞,同样是《朝花夕拾》的一个文体要素。儿童叙事在一定程度上也打通了童心童语与成人世界的内在联系,使得鲁迅的儿童本位观得到了文体形式上的还原与坐实。实际上,《朝花夕拾》的整体表达风格都是大悖于所谓“文格”的,追忆童年往事却又带入时事,意在批判传统文化却又沉溺于考镜文献源流,讽喻中偏多絮语,爱憎间屡有闲趣,这种任意推展的笔墨最终成就的是《朝花夕拾》更加贴近那种无所用心的有趣之童心而非急功近利的现实之感兴的文章体式。文章做法即是人生姿态,鲁迅这种越出主题规范和结构模式的自由发挥,正是他所看取的文章境界,自然也是人生自由的一种形式还原。《朝花夕拾》这些直写作者兴致与趣味的笔墨,既是在追索童年可能的记忆,更是对今昔孩童顺乎天性、痛快生活的理想境界的追摹与仿效,虽不能至,修辞可达,《朝花夕拾》至少在伸展自如的文体形式上表达了鲁迅期许的儿童世界的理想样貌。 正文 不同于《呐喊》《彷徨》,也有别于《野草》《故事新编》,鲁迅的《朝花夕拾》在研究者那里较少得到思想史视野中的引申,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这部散文集也并不居于显著位置。《朝花夕拾》往往更多地在传记研究意义上被吸收和征用1。实际上,这种阅读与接受的惯性倒是为我们预留了不少感受鲁迅文本的空间,比如我们较少细究的鲁迅的文章风格与精神趣味2,在《朝花夕拾》里其实有较多的流露,儿童叙事作为鲁迅创作伊始既已使用且在日后写作中不断实践的一种修辞,更是成为了《朝花夕拾》的一个文体要素,这一要素无论在主题学意义上还是在文章的形式层面,都颇具可阐释性,而且,儿童叙事在一定程度上也打通了童心童语与成人世界的内在联系,使得鲁迅的儿童本位观得到了文体形式上的还原与坐实。 孩童话语中的爱憎作为一部“从记忆中抄出来的”3忆旧文集,《朝花夕拾》自然意在追摹过往的旧事与人物,除了《藤野先生》《范爱农》两篇所记时间偏后,其它8篇大致都是基于鲁迅的童年经验与记忆写出的,孩童的话语也就成为直接或潜在的叙事动力。不同于差不多同时期的冰心式的儿童叙事,《朝花夕拾》中的孩童话语并不追求清新纯粹,而是始终夹缠在叙述者谈古论今的杂文笔墨之中,文化批判与童心童趣相互映照,孩童的爱憎好恶自然而然地表露其间。《狗猫鼠》谈狗论猫,起首便笔涉时事,但真正的叙事重心还是后半的一段幼年经历,一个十岁的孩子沉浸在祖母讲述的猫虎传说中,在老屋中的老鼠跳梁的声响里想象正月十四夜老鼠成亲的仪仗,特别是饲养一匹隐鼠过程中的悲喜苦乐,凡此种种其实是这篇散文最具吸引力的部分。鲁迅当然赋予了笔下诸种动物以现实的寓意,但这种童年忆旧的笔墨铺展开来之后,作者“仇猫”的心理成因其实已经变得非常简单,就是基于孩童的不会掩饰的直接的爱憎,鲁迅也不愿读者在语义上一味求之过深,所以在文中两次自嘲自己对于“仇猫”成因的过度诠释,那些光明正大的堂皇理由如“猫的一副媚态”、“慢慢地折磨弱者”等,被鲁迅说成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都是近时的话”。联系到《朝花夕拾》的“旧事重提”动因,可以说表达那种孩童的意绪与心理更接近鲁迅写作的初衷。 儿童的心理世界简单直接,他们对身边成人的感情与态度当然抱着同样的天真期待,《朝花夕拾》中的此类叙事大都具体而微,既写孩童的满足与欣喜,也表达了孩子们不可避免的挫伤和失落。“阿长”是《朝花夕拾》中多次出现的人物,在《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篇目中均被写到。鲁迅对于自己的这位幼年保姆感情深沉,但在叙事中还是尽可能还原到一个孩童眼中的身边的女工,并且随着孩子感情世界的起伏变换,将“阿长”、“阿妈”、“长妈妈”等带有不同亲疏色彩的人物面貌细致表现出来。阿长是作者叙事中杀死隐鼠的真正“凶手”,在日常的陪伴中也有令人不悦的惯习,有关阿长这类无名的底层女性的叙事在现代作家那里非常普遍,尤其是与作家自己的童年叙事相关联时,不少人常常会选择性地回避一些经验,余下的自然都是打磨光滑的美善记忆。鲁迅却直写上述那些记忆中显得粗糙的部分,阿长甚至也因此显得有些可厌,但也正因如此,阿长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属于孩童话语中完整的形象,鲁迅在若干篇目中让长妈妈反复出现,相互指涉,她所讲述的“长毛”故事、美女蛇传说乃至正月初一的福橘,都构成了一个懵懂幼童日常世界的重要部分,这里面有怕有爱,有亲有疏,有喜有厌,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正常可信的长幼关系。阿长在《朝花夕拾》里有一个十分耀眼的时刻,那就是为鲁迅买来了朝思暮想的绘图的《山海经》,这是一个孩子念念不忘却屡屡被大人忽略的心愿,也是一件别人不肯做的事。阿长的形象在经历了作者曲折往复的长短叙事之后,到这里终于成为幼年鲁迅心目中的英雄。这个具有“伟大的神力”的长妈妈是鲁迅儿童叙事中真正能够呼应孩童的简单直接的感情世界的成人,也是鲁迅着力塑造的一个孩童眼里的可敬的人。与之相对照的是《琐记》中记录较详的衍太太,实际上,这个人物也是连续在不同文本中出现,鲁迅在写作《琐记》前一天,刚刚做完《父亲的病》,衍太太便是其中文末登场的重要人物。鲁迅在回忆弥留之际的父亲时,表达了对中国传统的死亡伦理的最初记忆和不满,正是“精通礼节的妇人”衍太太催逼着鲁迅大声呼喊原本已经沉入临终之前的平静之中的父亲,4这种惊扰不但加剧了死者生前的最后苦痛,也使得生者鲁迅陷入永久的懊恼与不安之中。鲁迅对这一童年记忆难以释怀,表现在《朝花夕拾》的创作过程中,便是紧接着写出的《琐记》,开篇便直言衍太太的种种行状,几乎是前一篇未尽意绪的直接流露。尽管如此,《琐记》中有关衍太太的记述还是坚持运用了颇为严整的儿童视点,鲁迅克制住了积存已久的厌恶,对人物并没有做出成人视界里的褒贬,而是将话语权交还给衍太太周边的孩童们。衍太太的恶意、病态乃至阴险在孩子们眼里并不能轻易地分辨出来,在她自己或者不少大人看来,可能也并不以为如何可恶,这其实正是鲁迅所要揭示出的中国的儿童所遭遇的日常的“暗伤”,周作人谈及鲁迅的《琐记》所涉本事时,就曾专就“看春画”一节做了评议:“拿春画给小孩看,一方面轻侮他的无知,一方面含有来斫伤他天真的意思。”5衍太太们就是孩子们身边的习以为常的普通人,惟其如此,这种暗伤随时发生也无从躲避。鲁迅在文中提及从衍太太那里流出的关于他偷拿母亲钱物的谣言,这种有意无意的中伤令人如入冰窖。鲁迅一生屡遭各式“暗箭”的伤害,他的诸种激烈反应其实也是源于幼年时的这种相似的创伤记忆。 不同于《朝花夕拾》中偶或出现的模糊的母亲形象,“父亲”在《五猖会》《父亲的病》等篇目中均得到直接表现。鲁迅早年的挫伤与苦痛记忆其实也都与父亲相关,出现在这些篇目中的父亲形象一方面是病弱的,另一方面又是刚硬的传统伦理秩序的人格化象征。鲁迅将这两个侧面置于孩童的观察与感受当中来表现。《五猖会》中看迎神赛会而受阻的孩子是鲁迅笔下最令人怅惘的一个儿童形象,相应地,那位站在孩子后面的威严的父亲也就成为鲁迅写到的最令人侧目而又令人叹息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讲述这个颇具“审父”势能的故事时,并没有让这一势能顺流直下,转为激烈的动能,而是将一切归于一个幼童的眼中,使事件的起承转换均成为令人费解的一个过程,这应该是彼时孩童的真实感受,孩子无法理解成人秩序中的那些扭曲与异化,鲁迅采取引而不发的语式,既还原了一段难以释怀的记忆,又强化了文本的语义张力。 如果说《朝花夕拾》中有一个较为正面的“父亲”形象的话,那么《藤野先生》颇值得注意。虽然藤野先生在鲁迅笔下仍然是一个与瘦弱的父亲形象相似的长者,但在精神与人格层面已经成为被鲁迅所肯定甚至敬重的人物。《藤野先生》是记录留学青年鲁迅往事的名篇,其文其事虽然不宜被看做孩童的话语,但不妨看做鲁迅对儿童成长所需要的正面力量的某种期许,换句话说,如果儿童的成长中需要一个父亲的话,藤野先生就是一个样板。鲁迅表现的这段著名的异国师生情,既是留学生活的某种写照,也是童年时代中缺失正常父爱的鲁迅自觉不自觉的情感投射的产物。更准确地说,鲁迅在自己的幼年成长中其实缺少一种类似“精神父亲”的催生力量,现实中的父亲固然不乏儿女温情,但《五猖会》式的传统“严父”并不能带给孩子理解与尊重,当然也最终不会使孩子感受到爱与勇气。在鲁迅的记叙中,藤野先生所教授的医学知识并不重要,真正带来深远影响的是藤野先生的平等意识、严谨态度和人性之美。这种质朴美,连同《范爱农》式的率真质直之心,其实也都符合《朝花夕拾》整体语境中借由孩童话语所传达的爱憎判断。 文体还原中的情味 作为断续写成、陆续连载的专题忆旧散文,《朝花夕拾》是鲁迅文章中较少激烈气味的作品,鲁迅称之为“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集子中各篇的文体也被鲁迅视为“很杂乱”,且归因于写作时间长、环境也不一。实际上,无论是作于相对较为安逸的北京寓所时期的两篇,还是流离避居中的作品,包括心绪不良的厦门大学时段所做的末后五篇,都没有明显的写作语境所导致的文体差异,所以,鲁迅作如是说,与其说是在解说自己的文章体式,不如说是言明文集的写作过程,这也是文集“小引”的题中之义。如果说《朝花夕拾》果真存在文体之“杂乱”,其实也并非见诸各篇之间的比较,而是体现于每一篇的内部,这也正是这部散文集在写法和趣味上值得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ibeichia.com/zbcjbxx/7311.html
- 上一篇文章: 同1分数,多5志愿高考分数的隐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