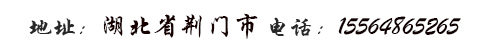坟头鬼话亲耳听闻的奇闻趣事,从山村到城市
|
#1.往日的故事 喜欢在网上看故事很多年了,看了很多朋友生花妙笔写出的稀奇古怪的故事。忍不住也想把自己亲身经历亲耳听闻的一些奇闻趣事写下来,凑个数,给大家分享,我自己也权作工作之余的消遣。我的老家在当地也算是人口数量比较多的村庄,坐落于鲁中南丘陵地区。村北是已经干涸的古雷泽湖,村南是一座以村庄命名的小山,据考证,此山另有名字,舜帝被继母赶出家后在此居住过,故又名妫停山。紧靠村南边的是一条东西无限延伸的公路,村北有一条日夜不息的繁忙铁路通过。 小时候,村里各家各户一样穷,娱乐极其匮乏,收音机都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大家的娱乐就是互相串门,他们经常聚在一起闲聊,各种各样古怪离奇的故事就在这种闲聊中不停的诞生,口耳相传,内容也不断变化、充实、丰富。对我来说,最好的娱乐节目,就是听大人们聚在一起讲故事。他们经常是一个人讲,其他人见缝插针地充实内容。有些故事不知年代,不知真假,有鼻子有眼,再加上讲故事的人和听众们一脸严肃惊恐,让人觉得每个故事都跟真的一样。大多数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村里的某人或者邻村的某位亲戚,偶然还有讲述人的亲身经历,更让我信以为真。 虽然听着这些不着边际、古怪离奇的故事长大,也貌似亲眼见过一些不知是幻觉,还是目前无法解释的异象,但是我故事中对所谓的“鬼怪”从来不怕。听母亲说,我未满周岁的时候,带着我下地干活,刮西风的时候就把我放在坟头的东边,刮北风的时候就把我放在坟头的南边。干完活,有时我睡得正香,有时醒了,自己咿咿呀呀的玩。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越来越不相信所谓的“神仙鬼怪”,也更让我相信鬼由心生,所有“神仙鬼怪”不过是人们想象出来吓唬自己,或者娱乐一下而已。 电影《罗生门》中有句话“我曾听说住在所罗门的恶鬼,因为害怕人性的丑恶而逃走。”其实,经历的多了,才知道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比故事里的鬼怪更可怕。 我看《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等志怪小说的时候,特别羡慕那些能遇上鬼友的人。现实中,世界上如此众多的人,没听说谁能交着一个鬼友,是时代变了,还是压根只是小说而已? 每次回到老家,都会听说曾经讲故事的人已逝,或者成为了故事中的人。故事中的老家也不复原来的模样,有些伤感,有些惋惜。把记忆中的故事记录下来,就当做对老家的一种怀念吧。 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前言不搭后语,颠三倒四,不成体统。 朋友们偶然看见了,权作一乐,不必认真,更不必较真。 #2.两个妇女 这是与我有关的最早的一个故事,母亲给我说过无数次,但是算不得我的亲身经历。 母亲年轻的时候,有哮喘病,当地方言称之为齁包(含有嘲笑之意,嘴馋吃得太咸引起的咳嗽)。我印象中的小时候,无论冬日夏天,母亲天天披着上衣坐在屋子里间(方言:堂屋内的套间)的床上,用被子围住半个身子,喉咙里发出吱吱的声音,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然后就是一阵阵剧烈的咳嗽。旁边的窗台上,摆着大大小小的褐色药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氨茶碱这种药,是家里的常备药。窗台下,是一堆白色的硬纸壳针剂盒子。那些空了的药瓶和针剂盒子也就成为了伴随我整个童年的玩具。 母亲说,一天,天刚黧黑(方言:傍晚),饭后她刚吃过药,坐在里间的床上喘得难受,也没看见门帘动,就看见两个妇女,都四五十岁,穿着白净布(方言:手工纺织的棉布,未加染色)的褂子,都包着白头巾,一个身材高点,一个身材矮点,走进了里间。母亲问他们:“你们是谁?你们是干什么的?”那两个妇女不理母亲,也不答话,径直走到床边就不见了。母亲感到奇怪,还没眨眼的功夫,怎么就藏起来了?母亲赶紧从床上下来,床底下、柜子底下、装粮食的陶瓮后头,到处寻找,什么都没有找到。母亲说,当时父亲就在外间,她问父亲,看没看见两个妇女进了咱家的里间?父亲说没看见人进来,什么都没看见,还说母亲看花了眼,说胡话。 据母亲说,从那时起,母亲就怀上了我。 有人说,那两个妇女是送子娘娘。如果说是送子娘娘,我未免有些失望,不凤冠霞帔也就算了,至少也穿个像戏剧电影中的戏服,给人点“神仙”的感觉吧,我多次问母亲那两个妇女到底什么装扮,母亲说就是当年普通农村妇女的打扮。 后来我想,说不定是来投胎的呢,我认为母亲更有可能是看花了眼。 #3.房梁上的手 记不清什么季节,也记不清几岁时候的事,但是清楚记得是上学之前。 那天我醒的比较早,天色还有些暗,我好像是被院子里软枣树(方言:君迁子树)上喳喳叫的灰喜鹊吵醒的。我躺在床上,看着被烟熏黑的屋顶和墙,墙上脱落的斑驳墙皮,构成了各种图案,我想象着那里是一座山,那里是一张人的脸,那里是一只鹿,那里是一条狗…… 我正无限遐想的时候,我突然清楚地看见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从我家房梁上伸下来。房梁下面放着一摞很高的煎饼,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有一摞煎饼,那摞煎饼是一家人小半年的口粮。我看见那只毛茸茸的大手在煎饼上抓了一下,过了一会,那只手又从房梁上伸下来,又在那摞煎饼上抓了一下,但是房梁上我没看见其他任何东西,只看见那只毛茸茸的手从房梁上伸下来。那只手有些像多年以后在动物园里才见过的大猩猩的手。 我指着房梁赶紧叫父亲:“大大(方言:父亲),他偷咱家nianing(方言:煎饼,这两个字实在不知如何写)。”父亲看了一眼,说了一句:“谁啊,哪里有啊,净胡说八道。”还在被窝里踹了我一脚。 我又看见那只毛茸茸的手伸出来抓了一次,我再叫父亲,父亲没再理我。 我到现在都有那只手的印象。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怀疑是我看墙皮图案产生的幻觉。 #4.黑橛子 这是我记忆中最早的一次亲身经历,那时我还没上学,约四五岁。 记得那是秋冬交替之际,天气比较凉,农忙也已经过了,一个月亮非常明亮的晚上,我和父母在奶奶家玩的比较晚。 我家和奶奶家隔着一条大街,我家住在一个死胡同的最里边,回家要绕过我家屋子的后边。 我们从奶奶家出来,月亮已经超过树梢,高悬在天空中了,父亲背着我,母亲在后边跟着,他们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 走到我家屋后的时候,我看见我家屋后那棵倾斜生长的大枣树下,路的正中间,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看不清是什么,像是倒扣的一筐猪粪。我指着那堆东西告诉父亲:“那里有一大堆猪粪。”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情景,还是觉得有人在那里倒扣了一筐猪粪。父亲看了一眼,他像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父亲低声向母亲说了一句:“快走。”我盯着那堆黑乎乎的东西,想趴在父亲背上,不知为什么,我却被母亲抱了过去,我们急匆匆的回到家里,一进大门,父亲立刻把大门锁上,赶紧上床睡觉。 第二天我被洋匣子吵醒,父亲和母亲早就醒了,他们坐在床上聊天,我听见母亲问父亲:“昨天晚上在屋后头,你干嘛把孩子扭(方言:拧)哭?”父亲说:“我没扭他。”母亲说:“你没扭他,那他怎么哭了?”父亲争辩说:“我真没扭他,正好好的我扭他干么?” 可是我明明记得昨天晚上在屋后面父亲没扭过我,我也没哭过,他们为什么说我哭呢?后来和母亲偶然聊起这事,她还是说我莫名其妙的哭了,她就以为是父亲扭的,这时父亲都会极力争辩从来没扭过我。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我没哭,父亲也没扭我。 过了几天,母亲听本家的一位二大娘说,和我家隔着一条小路的后邻居,那天晚上送邪神,也就刚办完送邪神仪式,我们就过来了。左邻右舍都听见了我的哭声,都给我母亲说,不是父亲把我扭哭的,是被黑橛子吓着了。 我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父亲没扭我,我也没哭过。至于那堆黑乎乎的东西,我还清楚地记得它模样,我一直觉得那就是一堆猪粪。 #5.桃树上的人 还是学前,五六岁时候的事。 东邻居的大门外,有一棵倾斜着长得很矮的桃树,树干有小腿粗细。这棵桃树就是当地常见的小毛桃,结的桃子不能吃。每逢春天,这棵桃树上就稀稀拉拉的开出几朵淡粉色的桃花。 初夏的傍晚,吃过了晚饭,父亲、母亲和东邻居家的大人们,在东邻居家大门口闲聊,我和东邻居家的孩子们追逐游戏。正玩着,我看见倾斜的桃树杆上蹲着一个人,清晰的记得,那个人就是一个黑乎乎的身影,看不清是男是女,就是一个黑乎乎的人形的黑影。他不是趴在树上,也不是站在树上,而是蹲在树上。我指着桃树告诉大人们:“你们看看,一个人在桃树上蹲着呢。”一开始大人们没在意,我看那个人蹲在桃树上一动不动,我拉母亲说:“娘,你看看,一个人在桃树上蹲着。”大人们停下聊天,母亲问我:“哪里?”我指着桃树上的人影说:“你看,那不是吗?他在桃树上蹲着呢。”他们顺着我指的方向看了看,立刻慌张的招呼孩子们回家,父亲和母亲拉着我赶紧回到家里,锁上大门。 很长一段时间,晚饭过后,都没有人敢在东邻居的大门口玩。 后来,我问母亲看到了什么?母亲说什么也没看见,我不信,再追问,母亲就骂我:小赊孩子,别胡说八道。问父亲,父亲也说没看见什么,我不满的说:那你们干嘛都跑回家? 现在我突然明白过来,人们最恐惧的就是不可知的东西,就因为他们什么都没看见,才吓得跑回家的。即便是我当时随便说的瞎话,他们也会害怕。 #6.墙根的妇女 应该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麦收刚过,晚上村里有电影,那时候的电影不是《地雷战》、《地道战》就是《南征北战》。 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不知什么原因吵了几句嘴。他们吵架简直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几乎每天都会吵架,小时候我经常被他们吵架聒醒。父亲和母亲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左邻右舍到我家劝架也是很经常的事。他们这个习惯到我成年结婚后也没改,一直吵到父亲去世,真正是吵了一辈子。 印象里那天放的《南征北战》。电影散场后,父亲背着我回家。我清楚记得那天晚上月色朦胧,月亮有一个很大的晕。到了家门口,父亲一摸大门是锁着的,母亲还没回来,一直都是母亲带着唯一的一把钥匙。父亲背着我到母亲经常串门的几户人家找,没找到母亲,又背着我回到大门口,一摸门锁,还是锁着的。父亲嘴里开始不干净了,骂骂咧咧,焦急地说:“你说你娘去哪里了,还不回家?”这时,我看见西墙根有一个妇女,高矮跟母亲差不多,好像在哭,拿着一只白色的手帕在擦眼泪,我指着那个妇女说:“俺娘不是在那里吗?”父亲说:“在哪里?”我指着说:“在那里,还光擦眼泪呢。”父亲看了一眼,也不说话,背着我转身赶紧走出胡同。 父亲找了好几家,终于在一个母亲平时很少去的刘姓电工家找到母亲,找到母亲的时候,母亲正和人家聊的起劲。父亲说了母亲几句,母亲反驳了几句,一起回家,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父亲的紧张,父亲左顾右盼,轻手轻脚,但是我没再看见西墙根的那个人影。 现在想起那个人影,感觉就像现在的投影仪投射到石头墙面上一样,不是很清楚,也看不清面部,但是手里擦眼泪的白色手帕,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7.夜半碾声 村里共有两台碾,北半个村庄共用一台,南半个村庄共用一台。南半村的这台碾在我家老宅西墙外头,由村庄南半部分的所有村民共用。 那时我家还住在老宅子上,我大约五六岁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夜里闹鬼特别凶。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家西墙外边的碾有时就会发出滚动的响声,听上去滚动的比平时要快,像是有人在匆匆忙忙碾东西,还有时传出几声呜呜的怪叫。在寂静的夜里,声音显得特别响,就像在耳边一样。 附近的村民都能听见。 第二天,村民们三五成群,面色惊恐地讨论昨夜发生的怪事,免不了添油加醋,衍生出好几种说法,有的说是鬼轧碾,有的说鬼穿着一身孝服(方言:白色丧服),有的说那鬼的脸一寸宽一尺多长,有的说只能看见鬼的上半身,看不见下半身,有的说那鬼没有脚后跟,在月亮底下没有影子,有的说亲眼看到过,那鬼跑起来一跳一跳的,有的说那个鬼是从碾盘底下钻出来的,就住在碾底下,还有的说鬼是从西南山上下来的,甚至精确的指出鬼来的路线。越说越玄,越传越吓人。至此,每天轧碾的人变少了,每天晚饭后,大街上不见人影,家家户户赶紧关门,串门的也不见了,大街上比扫过的都干净。 碾声和怪叫声,隔三差五的就会出现一次。因为离我们家特别近,我们听得特别清晰。碾滚动的时候,“鬼”走起路来听上去很有节奏感,一脚轻一脚重,给人感觉,好像真的没有脚后跟。碾不滚动的时候,不时传出呜呜的叫声。每逢这个时候,父亲和母亲都会从床上立刻做起来,一声不吭,也不敢点灯。我则把头缩进被窝,抱紧母亲的胳膊。不知有多少人家,在被窝里蒙着头瑟瑟发抖。 一个月圆之夜,月非常明亮,我记得依稀能看见窗外的树枝。到了深夜,碾声伴随着有节奏的脚步声又响了起来,一阵激烈的滚动声,接着几声呜呜的怪叫。母亲穿衣服起来,父亲紧张地小声问母亲:“你干什么去?”母亲压低声音说:“我扒墙头上看看这个鬼什么样。”父亲拉住母亲,不让她去。母亲披上外套,小声说:“我就偷偷看一眼。”父亲拗不过母亲,叮嘱一句:“你可别叫鬼看见,鬼再跟到家里来了。”就让母亲自己出去了,父亲紧张的浑身发抖。 外面几阵碾声,又是几阵怪叫声,母亲没有回来,父亲穿上衣服,想出去看看母亲,但是又不敢去,在床边紧张地站起来又坐下,扒着窗户往外看,也看不清楚母亲在什么地方。外面的响声终于停止了,恢复了夜的寂静。母亲回来了,父亲紧张的声音都发抖了,问:“怎么样,看见什么了,鬼没看见你吧?”母亲呵呵一乐,说:“没看见我,睡觉。”父亲也不敢多问,一脸狐疑的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父亲问母亲到底看见了什么,母亲说,是瘸子干的。瘸子是我的一个本家长辈,都三十多岁了,还是孤身一人。她看见瘸子披着一条白床单,从家里跑出来,推着碾转几圈,叫几声,跑回家,过一会,又披着传单跑出来,推着碾转几圈,叫几声,又跑回家,反复几次。深一脚浅一脚的脚步声,就是瘸子走路一步一颠的声音。父亲愤怒地骂了一句。 很快,村里人都知道了“鬼”的真相,年长的老人看见瘸子,笑骂他一句:“你这个小赊孩子,真不是个人。”他略显尴尬地嘿嘿一乐。自此,夜里的碾就消停了,也没有了呜呜的怪叫声、 晚饭后的大街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8.床边的红脸大汉 我家在村南不到一公里处,有二亩苹果园,苹果快成熟的季节,需要有人住在果园里看护,以免有人偷摘。在果园的西南方向,离果园三十米左右,是另一个村庄陈姓家族的墓地。 父亲看果园也要叫上我做伴,他自己一个人害怕,一到苹果成熟的季节,我就和父亲住在果园,一住就是十多年。 我和媳妇刚结婚的时候,我让父亲回家住,我和妻子看护果园。 我和媳妇住在果园里,离村庄比较远,没人打扰,过的悠哉乐哉,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虽然贫穷,但是还觉胜过世外桃源。提起那段时光,妻子也是非常怀念。 每天早晨六点半,我起床后上班,媳妇继续睡觉,中午回来吃饭,晚上过只有我们俩的生活,就这样过了两个多月。 一天中午,我下班回到果园,媳妇显得很紧张,对我说:“你走了之后,我觉着一个人站在床边。”我问:“什么人?”媳妇说:“我觉着是一个红脸大汉,至少得有一米八高,他就站在床边看我。”我说:“你真看见了?”媳妇说:“不是,醒了才知道是做的梦,可是看得那个人特别清楚,他就站在这里。”媳妇给我指着床边,我仔细查看床边的地面,除了我和媳妇的脚印,没有其他人的脚印。 第二天,媳妇告诉我,我上班走了之后,她又梦见那个大汉了,他还是站在床边看着她。 我觉着真有问题了,我也真有点怒了。我看着那片墓地,觉着肯定是那里面的东西。 我随手操了根木棍,走进墓地,一边用木棍抽打墓地里的草木,一边大声咒骂,狠狠地说:“再去找我媳妇,别怪我不客气,我把你们的坟全刨了,把你们挫骨扬灰,别以为我做不出来,不信你们就试试。”我在墓地里面撒了泡尿。说实话,我还真不怕这些东西。 此后,妻子再也没梦见过那个红脸大汉。 俗话说,鬼怕恶人,这个“恶”,我觉得应该是指不怕邪魔鬼怪的胆量。很久以后,我再想起这件事,可能我当时的做法给了妻子以心理安慰,让她以为所谓的“鬼”被我吓住了,她心里感觉踏实,自然也就不会再梦见所谓的“鬼”了。 #9.神童 早些年在当地有一个名气极大的神童,认识我媳妇后才知道,这个神童还是媳妇不知关系有多远的一个亲戚。 关于神童的传说很多,最出名的一个,是某村一人,带了五十个鸡蛋,求神童看病,那人觉得一个孩子,还说不上是否灵验,心疼这一篮子鸡蛋,于是在半道上扒了个坑,埋起来二十个。找到神童,神童说什么也不给看。他亲眼看到神童给别人看病时一个个说得都很准。从中午一直求到晚上,神童就是不看,那人无奈,哭着要走的时候,神童说:“你回去的时候,别忘了路上埋的二十个鸡蛋。” 这个神童,我亲眼见过,也亲眼见过他的神通。 年暑假,一个家住县城附近村庄和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他家人不知从哪里听说神童很灵验,就托我带他们过来。 我们上午到了神童村庄,来找神童的人很多,外省市的人都有,果然是神名远播。 神童不愧为神童,架子很大。神童并不是老老实实在家里给人救危济困,指点门路。他是一个很胖的顽皮男孩,村里山上到处跑,跟在他屁股后的是一群村里的孩子,孩子后面就是一帮虔诚哀求的大人,那场面蔚为壮观。等到神童大概累了或许饿了,才跑回家,趴在他妈妈的耳边一阵窃窃私语,然后他妈妈像是得到了神示,开始给人查看过去、预知未来、开出药方。神童的其他家人则端出一小铝盆拌好菜的面条,神童就在众人的围观之下,快速吞掉那盆面条,如果这时候有人出声恳求,神童则停下筷子,斜眼怒视,看得出声乞求的人心里发毛。吃完面条,神童带着那些村里的孩子继续满村庄玩耍,后面再跟上另一群等得心焦的大人。 中午,我们在神童家附近的私人小商店买了两包饼干、四包面包充饥。打开饼干,饼干已经被虫蚁蛀空,全是粉末,面包也全是霉点,一看饼干包装上的日期,已经过期三年以上。 我们一直等到傍晚,来求神童的人渐渐散去,从屋里面传出话来,仙家已经累了,今天不看了。同学的母亲和婶子不停哀求神童帮忙看看,神童并不答理,同学的母亲和婶子差点给神童跪下了,同学的母亲又是递烟,又是送钱,哀求了好大一会,神童伏在他妈妈耳边又是一阵窃窃私语,神童的家人开始收拾准备吃饭,神童的妈妈说:“过来吧,仙家愿意给你看了。”同学的妈妈和婶子差不多感激涕零了。 神童的妈妈烧上一小把香,闭目请神,片刻之后,开始看病。 神童的妈妈先说同学的母亲:你家拆过一个老房子,在梁上发现了一件镇物。同学的母亲赶紧点头:是是,是一个小磨,还有几个小陶罐,罐里装着五谷杂粮。 神童的妈妈说:你家上一辈有人挨过斗。同学的母亲赶紧点头:是是,他爷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挨过斗。 神童的妈妈说:你家东院有一棵长藤的东西,下面埋了一只扁毛的动物。同学的妈妈一脸茫然:我家东院是有一棵葡萄,下面没埋过扁毛的啥呀。 我和同学感到非常震惊,春天的时候,同学家不知因何死了一只鸡,扔了也就扔了,我和同学商量,不如埋到葡萄藤下当肥料,那一年那棵葡萄树长的非常茂盛,结出的葡萄远多于往年。同学立刻承认了:我们埋过一只鸡。同学的母亲问:是不是对家里不好?神童的妈妈说:没啥大事。 神童的妈妈又说很多过去之事,基本都确实发生过。 最后,神童的妈妈说:不用看了,你家没什么事。 然后给同学的婶子看,同学的婶子有心绞痛的病,我们这次来,主要就是给同学的婶子看病。神童的妈妈说:你家搬到新房子,当天晚上,大吉大利就被人一把抓走了。同学的婶子非常惊讶:对对,搬到新房子,一只大红公鸡,得有七八斤,当天晚上就让人偷走了。 神童的妈妈说:你家是个半截墙,谁家盖房子垒半截墙啊。同学的婶子说:对对,那堵墙,我们和邻居一家垒了一半。神童的妈妈说:那就是半截墙。 神童的妈妈又说了很多,都确有其事。时间久远,其他的我想不起来了。 最后,开出治疗心绞痛的药方,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药方中一味奇特的药,我观望了大半天,每个人看病后开的药方基本上都有这一味药,那就是:一截棕绳。棕绳在我们当地方言中,是指一切比较粗的绳类,不管是什么材料。同学的母亲和婶子追问:是不是就是那种很粗的绳子?神童的妈妈说:就是那种粗的棕绳。同学的母亲和婶子再次追问:是南方那种粗绳子?神童的妈妈说:就是那种粗的捆车的棕绳头,一截就行。绳的确切材料,没问出个所以然。 不知道同学的婶子后来用没用那个药方,不知病好了没有。 好几年后,有人说,其实神童的妈妈是神婆,有神通的是他妈妈,他妈妈只是借儿子宣扬神通而已。也有人说,神童的话,别人听不懂,只有他妈妈能听懂,他告诉妈妈,妈妈然后去给人解释。去求神童的人送的食品,神通家人都拿到他亲戚开的小卖店里再出售,有的在小店里买了送给神童,神童家人再送回小商店,怪不得我们在旁边的小卖店能买到过期三年以上的饼干和面包。 神童上初中后,听说学习很差,神通一点都用不上了。 再后来,听说神童已结婚生子,名气已大不如前。 现在回老家,已经听不到关于神童的任何传闻。 #10.看书入魔 我初中的一个同学,那时我们关系非常好。他的经历,有点像王宝强主演的电影《Hello!树先生》中的“树”。看这部电影时,让我想起了这位同学,我赞叹王宝强的演技,真是演到了骨子里,经历过的人,会看得更明白。 初中时,夏天,晚自习后,我们一起到村南野外的一个水**桥上乘凉。 那时,他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有关气功的书籍和杂志,偶然到了城里我才知道,那年代每个书店、每个卖书的小摊上都能找到这类书籍。我们一起研究,一起打坐练习。那时候气功风靡大江南北,香功,一灯法师,还有什么能控制天气、遥控治病的,能隔空传物的,等等,很是神奇。以前,一到冬天,我的手就会冻出泛白的疙瘩,天一暖,就奇痒无比。我坚持练了一年多的“水绵掌”,功夫一点没练出来,倒是冬天再也不冻手了,真是意外收获。 后来,我上了高中,他没考上,在家务农,但是我们关系还是很好。每次我从县城放学回家,都要找他玩。我不在家,他经常到我家借我的书看,我告诉过母亲和父亲,我的书让他随便拿。 有一年春节过后,大概三四个月没看见他,据他的母亲说,他跟人出去打工了。 约三四个月后,母亲给我说他回来了,听人说,他一出远门就生病,实在没办法,他把带出去的被褥全扔了,人跑回来了。那时候,被褥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财产,他这种行为,有点败家子的意味。 我去找他,他变得有些憔悴,低着头,不停地变换着姿势搓动双手,不住叹气。 到了高三,学习较紧,半个月才回一次家。 一天中午,我回到家,母亲告诉我,我的这个同学疯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再次确定,是我的这个同学疯了。 我回家一星期前,他借走了我的《红楼梦》。传闻,两三天前的一个凌晨,大雾,天还没完亮,有人看见他一个人在铁道北边的北湖(雷泽湖)的麦地里疾走,天亮了他才知道回来。 他父亲以为他看《红楼梦》入魔,愤而把书撕掉。这几天,听说他一直处于疯的状态。 我赶紧去看他,进门看见他的母亲,他的母亲阴沉着脸,我问同学在哪儿,他母亲向屋里努了一下嘴。屋里很阴暗,我看见同学围着被子坐在床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听见我进来,他又呆呆的看着我,我问他:你没事吧。他显得很机械说:没事。此后没有多说一句话,他又盯着地面,一动不动,像是陷入了沉思,像一尊很有颓废感的雕塑。原先,我俩在一块无话不谈,现在已经是无话可说。 我坐了一会,告辞出来。 后来,又听母亲说,他家特别穷,交完公粮以后,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了。没有办法,他父亲晚上偷偷出去,到比较远的地方要饭(方言:做乞丐,乞讨),回来的时候,白天不敢回村,在村外的沟渠里等到天黑了再回家,怕村里人见了笑话(方言:嘲笑)。 这让我想起,有一次我到他家,看见他家饭桌上摆着一些煎饼,各种颜色、各种口味的都有,当时我还纳闷,他家怎么做了这么多种类的煎饼,一般人家为了省事,一般只做一种口味的煎饼,比较讲究的人家,也只是把一种粮食做成酸甜两种口味而已。我回家给母亲一说,母亲一愣,说:可能是要饭要来的吧。我才明白,那是乞讨来的。 再后来,我想,我这个同学真的是看《红楼梦》疯的吗?如果真是,那他也是《红楼梦》成书以来看书成疯的第一人了。但是我更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贫穷,是贫穷埋葬了他的理想,是贫穷压垮了他的精神世界。村里靠出去乞讨生活的,估计也就他这一家吧。一个充满理想的小伙子,面对活着的残酷,所有的理想全部破碎成渣,谁能受得了? #11.奇怪的衣服 这是媳妇的侄女和侄女的丈夫亲口说的他小两口的亲身经历。 他们现在住在公路旁的一栋二层小楼上,他们的老家,是山南边得一个小村子。 年夏,她和丈夫开车去老家办事,回来的时候丈夫开车,已近傍晚,不开车灯也能看清道路。 过来山口之后,很快就走到一条笔直的约七八百米的下坡路,这条下坡路,是修在以旁边村庄命名的山的北坡,比较陡。十年前这条路还是土路,现在修成了水泥路,它是山南边各村庄通往山北的一条重要通道。这条路和东西方向的公路相交之后,再往北走一百米左右,就是一个五天轮流一次的集市。 丈夫正开着车,突然觉的天一下就黑了,丈夫打开车灯,只能看见路面,路两边的树都看不清楚,他觉得开了很长时间,平时不到一分钟就走完的路,怎么开了很长时间,还没到那条马路?丈夫不停劲揉眼睛,妻子感觉不对劲,让丈夫下车,妻子来开。很快就到了那条公路,很快就回到了家。 到家后,妻子问丈夫开车时怎么回事,丈夫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就是觉着身上有些冷,有点怕光。 简单洗漱,上二楼卧室睡觉。 半夜,妻子被丈夫惊醒。见丈夫坐在床边不停叹气,妻子没好气的问他:“你干嘛呢,都几点了,还不赶紧睡觉。”丈夫叹着气说:“睡不着,那里站着一个人。”丈夫指着衣架说,妻子吓了一跳,看丈夫指的地方,只见衣架上挂着的一件丈夫平时穿的风衣。妻子说:“那是你的风衣,哪有什么人?”妻子又躺下睡觉,丈夫还是不睡,妻子问他:“你怎么还不睡?”丈夫说:“那个人还在那里站着呢。”妻子没好气的起来,把风衣从衣架上拿下,扔在椅子上,说:“这回没人了吧,赶紧睡吧。”丈夫依言躺下睡觉。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妻子又被丈夫吵醒了,丈夫还是坐在床边叹气,妻子又没好气的问他:“你又干嘛呢?不赶紧睡觉,真让你烦死了。”丈夫指着椅子上的风衣说:“睡不着,那个人在椅子上坐着呢。”妻子这下也感到怕了,一时睡意全无。 挨到天亮,妻子赶紧找婆婆公公,婆婆公公到处打听,找能请神送鬼的神婆。打听到东北方向的一个小镇,有位比较灵验的神婆,妻子开车赶紧带公公去找神婆。到了神婆家,少不了香火钱,神婆下了一会神,告诉他们:“是一个找不着家的孤魂野鬼,跟着你们上了二楼,转转悠悠的找不到出来的路,送走就行了。”妻子和公公带着神婆回家,做法送鬼。送完鬼后,丈夫觉得很疲劳,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像干了三天活没休息,躺床上就睡了。 一家人对神婆千恩万谢,要把神婆送回家,妻子表示她自己开车送就行了,路也不远。公公不放心,随车一起去送。 送完神婆,快回到家了,车需要掉个头,妻子说:“掉头的时候,我还专门往右边看有没有车,大白天的,看得很清楚,真的没看见有车,刚一掉头,一辆大货车,就像凭空冒出来一样,一下蹭到车头上,把保险杠都蹭掉了,多亏我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还不知怎么样呢,当时我都快吓死了。” 小两口给我们讲着当时的种种情景,还是一脸惊恐,媳妇的侄女说:“从小到大,头一回遇到这种事,以前光听人家说,这回亲眼见着,你没见当时**(她丈夫的名字)眼睛直勾勾的,脸色特别不正常,可把我吓死了”。我听着他俩绘声绘色的讲着,我感觉到非常可惜,我一直想见见所谓的“鬼”,可是一直没有机缘见到,如果能交个“鬼友”,更是求之不得,如果他们提前告诉我,我还真想把这个所谓的“鬼”带走,我要好好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到底会不会传说中的各种变化,传说中遇到的各种奇异之事,是不是它们这一类搞出来的,唉,实在可惜。 #12.凶路 上篇提到的这条路,一溜大下坡的路,从小就听过不少在这条路上发生过的故事,也有近些年发生过的重大事故。 年,在这条路上发生过一次严重的事故。 我村有两家人关系不错,一个是我小学同学的哥哥,一个是我另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同学的哥哥买了一辆二手的简易吊车,这种吊车专用来为农村盖房子吊个建材预制板什么的。本来是同学的哥哥自己干,但是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上了同学的父亲帮忙。 年夏,他们在山南一个村庄干完一天活,开吊车回家,走的就是这条路。 机动车下这个大下坡,肯定要一直踩着刹车,谁知刹车失灵,车辆越来越快,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直往山路下冲,吊车眼看还差几十米就快冲到与公路的交叉路口,同学的父亲慌乱之中跳车,没成想,开车的同学的哥哥可能怕吊车冲向路口与过往车辆相撞,惊慌失措之中打了一把方向盘,失控的吊车从同学父亲身上碾过,吊车冲进路边的沟里。同学的父亲当场被碾碎,同学的哥哥被方向盘刺穿胸腹,二人当场死亡。据见过现场的人说,非常惨烈,同学的父亲几乎成了肉渣,已经看不出人形。 人死后要发丧(方言:办葬礼),同学的父亲家要求同学的哥哥家赔钱,不赔钱闹着不让发丧,结果是同学的哥哥兄弟几个凑了钱赔给同学的家人,此事才算了结。 其实刹车失灵也不奇怪,农村那种及其简易的吊车,没有驾驶室,更谈不上主动被动安全装置,就是一个框架,装发动机,弄个绞盘,焊个支架,装上四个轮子,弄个方向盘,就成了一辆吊车,刹车是最古老的鼓式刹车,说不定发动机、轮胎、刹车装置等等都来源于报废车辆,没有任何安全性可言。这条大下坡的路,和东西方向的繁忙公路交界的交汇点,也是事故的多发地,隔三差五就出一次事故。本来这条公路车辆就比较多,跑在这条路上的车还大部分是重型大货车,再加上交汇点的北侧就是个五天轮流一次的集市,每逢集市那一天,附近乡村的老老少少都来采购蔬菜、生活用品,人流量非常大,没有红绿灯,再说农村人很多都不懂交规,大都没有什么交通安全的观念,自然造成这个路口交通事故频发。 小时候,听大人讲,我村一个人,刚过完春节,他到山南的一个村庄走亲戚。喝了不少酒,回的也比较晚,约晚上八九点钟吧。他过了山口之后,就看见眼前一条笔直光滑的大路,他就顺着这条大路走。这条路,看着好走,可是走起来却颠簸难行,走了很久也走不到头,累得他浑身冒汗,自行车推都不住,他就扛在肩上,走亲戚回来的礼品也不知丢到了哪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了大半夜,也没走到公路。等到鸡叫,他才发现,他一直在一片红薯地里转圈,把地都踩光滑了。亲戚回的礼就撒在地里。 还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中的人物没有具体的村庄和姓名。 说得是早些年,一个拾粪的老头,人很勤劳,起得很早,天刚蒙蒙亮,背着粪筐,拿着粪叉,走到这条路,正拾着粪,看见前面背对着他站着一个老太太摸样的人,他好心的问:“大嫂,恁起这么早。”那人没有反应,老头以为那人耳背,走进了又问:“大嫂,恁起的怪早的。”那个老太太可能听见他说话了,也不吭声,转过脸来,老头吓得魂飞天外,扔了粪筐和粪叉就跑,那人的脸有一寸宽一尺多长。其实,我认为这个故事是大人们瞎编的。 脸有一寸宽一尺多长这个怪物的形象,据大人们讲,在小山的东边的那条路上,也就是我追过“鬼火”的那条路上也出现过,不知是谁遇上的。小山东边那条路是我村通往山南各村庄的要道,年刚修成了水泥路。 年暑假,每天吃过晚饭,散步的时候,我和爱人都要领着孩子们绕过一座小山的南侧,然后爬上那座山。那座山的山顶正中,有一个盗墓贼挖的很深的盗洞,看不清下面是否有棺材,后来听说,盗墓贼从这里盗走一把宝剑,不知道真假。山顶上还有一处不知什么部门设置的标识。第一次下山走这条路的时候,天快黑了,我看见路西的谷子地里有一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怕吓着孩子们,没声张,我心里暗暗戒备,走进了才看清楚,是用来吓鸟雀的草人。每次下山的时候,都接近黑天,我们走的都是这条“凶路”,一路上没有任何感觉,一整个暑假,并没有遇到任何鬼怪。 #13.姥爷 年4月9日上午11:46分,母亲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直接就说:“你十月一回来上坟吧。”母亲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吓了我一跳。农历十月一日,是我们当地很重要的上坟的节日,甚至比清明节还要重要一些。 我问母亲发生什么事了,母亲语气显得紧张不安,说:“上午我和你二姨去看你姥娘了(姥娘:方言,即姥姥;我姥姥年已是99岁高龄),你姥娘还能聊天,我们正说着话,你姥娘突然眼就直勾勾地,一个胳膊就像被人拉着,直直的往外走,你二舅赶紧抱住你姥娘,你姥娘说你姥爷来叫她了,你姥娘一个劲往外挣,你二舅差点抱不住,我和你二姨赶紧烧香、烧纸、磕头,祷告让你姥爷赶紧走,别折腾你姥娘了,烧完纸你姥娘一会就好了。我给你说啊,你姥娘那个手脖子(方言:手腕)上还真有一圈发青的手印,把你姥娘的手脖子都攥肿了。可把我吓死了,从小到大头一回见这样的事。十月一的时候你要有空,还是回来给(方言:父亲)上坟吧。”姥爷去世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了。 母亲又说起刚过春节发生的事,母亲和她的几个兄弟姐妹去看望姥姥,姥姥从床上突然起身,径直往大门走,大家问姥姥干什么去,姥姥说:“我得走,(方言:父亲)来叫我了。”大家不信,都问姥姥:“俺大大在哪里,俺怎么没看见?”姥姥指着前面说:“这不是吗。”大家问:“咱关着大门,俺大大怎么进来的?”姥姥说:“从墙上爬进来的,从牛栏(方言:猪圈)后头爬进来的。”他们又是烧香又是磕头,姥姥才安静下来。 过了一天,我打电话母亲还在姥姥家,问母亲这些天姥姥有没有什么异常,母亲说,这几天又好些了,就是喘气呼噜呼噜的老吓人,母亲把手机放到姥姥嘴边,我从手机里清楚听见姥姥嗓子里呼噜呼噜的声音,还伴随着哼哼的呻吟声。 #14.墙根的人影 小飞蓬是一种常见的杂草,确切的名字应该是加拿大小飞蓬,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各地都能见到这种植物,特别路边地头,更是常见。当然,我所在的这所学校里,也是少不了的。每年绿化工都要清除杂草,可是这种杂草的生命力实在太强了,校园里还是到处都能看见。 前几年暑假后,学生入学前,约晚上八九点钟,路灯都已经亮了,我到单位办公室有事,途中要经过X夫馆,X夫馆几乎每个大学都有。 X夫馆的西侧,有一个进深约两米的夹道。借着路灯灯光,我老远就看见有一个人蹲在夹道口的墙根,我心里纳闷,他蹲在那里干什么,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我越走越近,过了办公楼,我向办公楼门口看了一眼,办公楼门口的保安还站在那儿,我转回头来再看夹道口那个蹲着的人影,那儿蹲着的人影却不见了,我一转头的功夫那个蹲着的人就消失不见了,跑得那么快?不可能呀。我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夹道口,我看见的是夹道口的墙根生长着几棵半米来高,缺水缺肥,瘦弱不堪的小飞蓬。那个人蹲着的地方,变成了一丛杂草。是我看花眼了?可是我明明看到的就是一个蹲着的人影。 一个星期后,学生开学了,这事我差不多快忘了。 一天上午,我和同事到南区检查,经过X夫馆西墙夹道口的时候,同事指着夹道里边说:“你听说了吗,情人节的时候,一个外校的小伙子,找X夫馆一个系的女生求婚,女生没答应,小伙子从X夫馆九楼到十楼的楼梯间窗户跳下来,当场就死了,就是这个位置。”同事指着这丛小飞蓬说:“当时那个男孩子的头就摔在这里。”听得我后背一阵发冷。 后来,这丛小飞蓬和夹道里边的小飞蓬都被绿化工清理干净了。我还是经常从这里来来回回,再也没见过那个人影。 #15.代号 昨晚和其他单位几位参加工作三十多年的师傅小聚。 他们聊着聊着就回忆起二三十年前的经历。 他们说,那个年代,也不知怎么回事,胆子太大了,现在想想都后怕。特别是处理很多意外死亡,其中一位粗略一算,处理过一百多起。 李师傅说,院里的那个小池塘,别看它小,里面出过不少事。多年前一个夏天的上午,那天李师傅值班,刚吃过早饭,正在值班室看报纸,院里一个整日游手好闲的家伙跑到值班室门口,全身抖得筛糠一样,说话也不利落了,他说在池里钓鱼,钓上一个人来。李师傅说不可能吧,你看见了?那人说看见了,真的。李师傅赶紧跟那人到池边一拉钓鱼线,可不就是个池永辉吗,是咱院里的一个老太太,每天起得特别早在公园里晨练,那天不知怎么回事,掉进池塘里淹死了。 刘师傅说,那个池塘很邪门,比如那一年,一个池永辉,是个bo士生,在那个小池塘淹死。你们都知道,深水区都被咱们用铁网子给封上了,只留了一个直径三、四十公分的口,水那么混,专门找那个口都不容易,他正好就卡在那个口里,怎么就那么巧?也该着他死吧。 刘师傅说,游泳馆也很邪门,自从游泳馆建成启用后,每年至少一个池永辉。多年前的一个夏天的晚上,游泳馆负责人跑到刘师傅单位,说游泳馆关门的时候,发现多了一套衣服。刘师傅说听见多了一套衣服,当时他的绿毛汗都下来了。到了游泳馆,刘师傅叫人拉着拔河用的绳子,从深水区的一头开始兜着池底拉。拉到中间的时候,咕嘟泛了一个水花,刘师傅说,下去捞吧,池永辉肯定就在那儿。 有一年,马上到年底了,游泳馆很幸运的没出事。某位领导高兴的说今年做的很好,没见到池永辉。结果第二天,池永辉就出现了一个,大家都骂某领导是臭嘴、乌鸦嘴。 刘师傅说前几年处理过一个楼疯,外面的一个小伙子,情人节的时候到咱们院里向一个女孩求婚,女孩没答应,小伙子杀了女孩,自己从X夫馆九层至十层之间的楼梯间窗户跳了下来。 我仔细问了跳楼的位置,正是我把小飞蓬错看成人影的地方。 刘师傅说还处理过几起刘见一。多年前,一个老学者,骑自行车过铁路开会,推自行车过铁路的时候,老人行动慢,自行车卡进铁轨,躲闪不及,被火车撞死。 李师傅说,那一年处理的那个饼,就是修体育馆外墙的那个,架子倒了,拍成了饼。那个年代报个意外,赔偿点钱就完事了,放到现在,层层追责,麻烦大了。 我听着很纳闷,刚才说的池永辉、楼疯、刘见一,是人的名字吗? 几位师傅说这是代号。他们对不同致死原因的尸体有个代号:水里淹死的叫池永辉,高空坠落的叫楼疯,剩一条腿的叫刘见一,砸死的叫饼,等等。 #16.莫名其妙的韩语 年夏,我和几个同事在我现在打工的某城市X道口的啤酒花园吃宵夜时,一个关系很好的同事讲的他的亲身经历。 约年左右,夏天,他和要好的哥们,一起去北X环边上一个平房区吃烧烤,大约喝到夜里十二点多,大家都喝了不少酒,他们顺着铁道边回家。走着走着,他突然就迷糊了,正和哥们聊着天就开始说起了韩语。他一点韩语都没学过,从来不会韩语,就莫名其妙的说了起来。他说当时说韩语的时候,好像说韩语就是说母语,特明白什么意思。朋友们把他送到宿舍。第二天醒来,一句韩语都不会了,只觉得头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周末回X碑店的老家,找神婆看了一下,神婆说他被一个韩国小伙子附了身,跟他做了法,当时头就不昏了,就是感到浑身乏力,躺在床上休息了一天才感觉好些。他一直纳闷,哪来的韩国鬼附上了他的身? 那次与他一起经历过韩语事件的几个哥们也在场,一提起这事,他们七嘴八舌地补充那天他说韩语的各种细节。 这让我想起约年前后,北X环上发生的一起严重事故,这个事故我亲眼去看过。一辆摩托车从铁道边东侧一条没有路灯的小路上(那条小路现在还在,不已经安装了路灯),自北向南高速撞在北X环粗大的护栏上,坐在摩托车后座的人从北X环上一头栽到接近十米深的桥下,当场死亡。我去看的时候,摩托车还卡在桥护栏上,死者已经用报纸盖住,路面上流了很长的血迹,报纸下露出一只纤细白皙的手,围观者都说死者是一个年轻女人。 过去近13年时间,我几乎忘了那次看见的事故,他的故事又让我想了起来,那次事故的死者,可能就是一个白白净净的韩国小伙子,而不是一个年轻女人。 #17.多事的铁路道口 就在韩国小伙出事的地点往北三、四十米,很多人从那里直接横跨铁路,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一个大家走习惯的路口。这条铁路的西侧就是南北走向的城铁大桥,在这个自然形成的铁道路口的城铁桥下,也自然有了一些修鞋、修理自行车、卖小饰品等等各种小摊位。 大约年夏天,那时候MP3音乐播放器非常流行。两个女学生,约有十六、七岁,一人带着一个耳机,共听一个MP3,挽着胳膊并排过铁路。一列通往X拉尔的绿皮火车快速驶来,铁路两边小摊点的小老板,还有在城铁桥下乘凉的人七嘴八舌的大喊:火车来了,快躲开。两个女孩似乎一点都没听见,火车把两个女孩撞飞出去,当场死亡,一个被撞的七零八碎,另一个还算完整,一个女孩的脑浆喷洒在路基的碎石上,修自行车的师傅说:那脑浆落在地上,一颤一颤的,好像还活着。 两个女学生死亡的照片,收集碎尸的照片,前几年网上还能搜到。 我亲眼看见两个女孩的家人聚集在XX园火车站,呆了有一个星期,也不知能够获得多少赔偿,听说很少,只有几千块钱的丧葬费。 在这个道口往南约百米之内,以前经常出现伤亡事件,听说的: 有一个骑三轮车送桶装水的小伙子,懒得绕远路,想横穿四、五道南北向的铁轨把三轮车推到对过,三轮车轮子卡进铁轨,火车驶来,小伙子想奋力把三轮车弄出来,结果,当场死亡。 这之前,一个某校的退休老学者,骑自行车要到对过某地开会,横穿铁路,自行车卡进铁轨,躲闪不及,也被撞死。 两个女孩出事之后,铁路两侧加装了非常结实的护网,行人要想到对过,只能走立交桥下,或者走专人值守的路口,再也没有出现过事故。 今年,这条铁路改造到地下,地面上的这条铁路已经废弃拆除,百年历史的XX园火车站也废弃了,有很多人去拍照留念。 由此看来,有些所谓的凶地,应该是没做好防护造成的,只要防护做到位,凶险之地也就不存在了。 #18.莫名其妙的跟头 女儿一周岁的时候,我就辞掉老家的工作,出远门打工了。 第二年暑假,女儿两周岁,我回到家里,闲聊的时候,媳妇给我说了一件怪事,媳妇带着女儿过了公路,去村南野地里玩,每次走到路边有几座坟的地方,女儿都会摔跟头。媳妇指给我看女儿膝盖上一处结了疤的伤痕说:“这就是前两天摔的。”我一听,当时就怒火中烧,我想起我妹妹十一岁的时候,在那附近骑着自行车也摔倒过,把锁骨摔断了,当时我也没多想。 我拿起头就往外走,媳妇一把拉住我,问我要干什么,我说:“没事,我去教训教训那几只孤魂野鬼去。”我知道那几座坟,是村里刘姓电工家的祖坟。 那几座坟离村子很近,我到了坟地,每座坟头上狠狠地刨了一头,指着坟告诉它们:“以后再敢让我女儿摔一个跟头,我就把坟全刨了,把你们的骨头全扔茅坑里。” 从那之后,女儿再也没在那里摔过跟头,后来我电话问媳妇,她说再也没发生过。 每逢假期回到老家,我去路南地里的时候,看见那几座坟还呆在那里。 #19.去世的表哥 听母亲说,父亲去世三天前,看见我一个去世的表哥,在我家大门后边站着,父亲还叫着那个表哥的小名问:“你怎么来了。”父亲指给母亲看,但是母亲什么都没看到。 那个表哥是父亲的外甥,两年前出车祸死的。他死的比较奇怪,他到我村来人情(方言:有人去世,举行葬礼时,亲戚都要出些礼金),他还没吃完饭,本来不想走,他们村有人借了一辆皮卡,车上的人都是他们村的,开车的司机跟他关系也不错,把他硬拉上后车斗,让他一起回家。过了东边那个村,那个酒驾的司机开着皮卡,撞上了停在路边的大货车,出车祸的时候,车上十多个人,其他人都没事,几乎连擦伤都没有,只有他,从后车斗窜出来,一头撞到大货车的车厢上,人当时就没救了。 父亲去世的前一天,大雾,父亲到村南的地里看庄家,回家跟母亲说他遇到村里的一个妇女,背着筐,那个妇女几年前因为种西瓜卖不出去,着急上火上吊而死。 隔了两天,父亲就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一个神婆给母亲说,父亲遇到那个妇女时,那个妇女迷了父亲的眼睛,意思就是使了个坏。 母亲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我在心里是抱怨母亲的,为什么不早给我说,父亲去世了才给我说,如果母亲早给我说,我绝对会立刻回家,别管到底是真是假,到底有没有关系,我肯定会去那个表哥的坟上给他点警告,至于那个妇女,我更会给它一个严厉的警告。管不管用不说,我肯定会干,万一有用呢? 这也可能就是人的命,父亲的阳寿也可能就到此为止吧。 #20.墙角上的钉子 我15岁那年的秋天,天气比较凉,我家从我生活了15年的老房子搬到了新宅。 有一天,父亲在堂屋的东里间东北角的墙上砸进了几根钉子,用来挂农具。过了片刻,父亲的眼睛开始又疼又痒,父亲让我看,眼白上出现了很多红色的小疙瘩。我去村诊所给父亲买了眼药,涂上不管用。父亲去找本家的一位大娘。等父亲回来,眼睛基本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从那个位置拔了一根钉子,父亲的眼睛又难受起来。父亲自己去了村诊所,拿了药,又吃又涂,还是痛痒难忍,根本不管用。父亲让我赶紧在家里找一枝脱了粒的高粱穗,和他一起拿着找本家的大娘,这位本家的大娘算是半个神婆,说她是半个神婆,是因为她有时做神婆之事,但是不会下神,有时灵有时不灵。这位大娘用高粱穗在父亲的脸上扫一扫,吹一吹,祷告祷告,把高粱穗烧掉,过上一会,父亲眼球上的红色小疙瘩就消失了。 这是什么道理,我到现在也没明白。 #21.附身 在老家农村,扶起人来(老家方言:鬼附身)似乎很常见。遗憾的是我从没亲眼见过,父亲亲眼见过,给我说过几次。 多年前,一天傍晚,也就七八点钟,父亲回到家里,说我大表哥扶起人来了(方言:鬼附身)。 本来大表哥和我本家的叔叔一众人等在大表哥家一起喝酒,大表哥突然就被附身了,父亲找大表哥有事,也在场。大表哥眼睛直勾勾地,说话的声音和我去世多年的爷爷声音一模一样,指着本家的叔叔,叫着他的小名,骂他不孝顺。附近乡亲听见异样都来了,众人摁住大表哥又是掐人中,又是祷告:老人家别折腾孩子了,到年到节多给你烧纸,少不了你的钱花,等等。我没等父亲说完,赶紧往表哥家跑,想亲眼看看鬼附身到底什么样子,可是进门看见表哥和本家叔叔以及一大帮左邻右舍,围着饭桌有说有笑的喝茶,就像没从来没发生过附身事件一样。 听父亲说,路西的一个男邻居,也被附过身,被附身后,也不知是哪里的口音,逮着谁骂谁,他父亲掐他人中,朝他脸上猛扇耳光才逐渐恢复正常。 这个邻居的南邻居,女主人也曾被附过身,口音明显是南方人,女主人家南墙外就是车祸多发的公路,应该是公路上出车祸死的人附了她的身。请了神婆,烧香烧纸,祷告一番恢复正常。 前年十月份,本村的婶子出车祸去世。近期回老家,听人说她大儿媳酒后经常被婶子附身,每次附身,都是以婶子的口吻说:忒冷了,这么冷啊,冻死我了。有人说,可能婶子出车祸时并没死,只是昏迷,以为她已去世,收在太平间的冰柜里冻死的。也有人说,这是婶子来要衣服穿,婶子去世的时候身上穿着夏天的衣服,披了一条床单,冬天到了肯定冷了。各种猜想都有。 其他附身的事件也听说了很多,但是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甚是遗憾。 #22.阴阳眼 我一个关系比较近的亲戚据说是阴阳眼,我和他在一起时,从没看出他是阴阳眼,他也从没表现出来过,可是其他和他经常打交道的亲戚都说他是阴阳眼。我仔细观察过他的眼睛,并没有什么异样。 以下事件我都没亲眼见过,听亲戚们说的。 听亲戚说,有一次他去了一下我一个本家的厕所,出来就给本家说:“你家厕所里有个桑木神。”据本家说,二十多年前,房子没改建之前,厕所里确实有一棵自然生长出来的桑树,改建房子的时候,就刨掉了。 还是在那个本家,大人不想让孩子玩麻将,就把麻将藏了起来,大人出去后,孩子们想玩,找不到麻将,正好这位亲戚在,让他看看麻将藏在什么地方了,这位亲戚看了一圈,说,在床底下。小孩们还真从床底下的鞋框里找了出来。其实,这件事,我认为要不就是这位亲戚看到大人藏麻将了,要不就是推理,看了一圈,最有可能藏得地方也就是床底下。 村里安装自来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挖铺设自来水水管的沟,还是在那个本家的大门口,还没开始挖,这位亲戚说:“这下面有两个棺材,对着头。”挖沟的时候,果然挖出两具不知年代的棺材,并且是对着头埋的,其中一个棺材里还有一支矛。 还有其他关于他的传闻,他经常给附近村民选墓地,看阳宅,断吉凶,至于他的阴阳眼,我一直半信半疑。 #23.小山顶的女尸 这是父亲给我讲过的故事。 早些年,四五十年前了吧,修村南边的这条公路,某级政府要求村里每家每户都要按人口交出路沿石,就是片状的大块石头。一时不好找这种石头,有人带领大家挖掘附近的无主坟墓,附近的无主坟墓大部分是用粗糙的石板搭成的,那正好用来做路沿石。我们这边沟区里经常见到不知年代的用粗糙石板搭成的简易墓,我曾经在山脚的沟里捡过几枚这种墓里的小铜钱,上面有“大泉五十(也可能是大泉十五)”字样。 后来我才知道,古墓中为什么会有铜钱。当地有一个风俗,去世的人入棺时,要在棺材内的四角各放一小摞硬币。原来这个风俗延续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关于挖墓,有各种说法。父亲说,挖到墓后,起墓(方言,撬开墓的上盖)的时候,要躲得远点,有时候起墓,有一股瘴气从里面冲出来,要是被这股瘴气撞上,不死也要得一场大病。 附近能挖的坟墓基本都挖完了,后来他们就到小山上挖,在山顶上挖到一座大一点的墓,起墓后,墓里一具女尸,跟活的一样,身上穿的是华丽的大裙子,一看就是富家太太或者小姐,里面有一根凤钗,不知让谁拿走了。那些衣服尸体见了空气,很快就变了颜色,变成了粉,风一吹就散了。 现在小山的山顶上还有几处被盗墓贼挖的盗洞,二、三米深,下面隐约看出破碎棺材的痕迹。 #24.二表哥的家 大姑姑家早年承包苹果园,赚了不少钱,给二表哥在公路边盖了一处房子。我觉得那房子在当时可以说是村里最好的。我偶然有事去他家,从外表上看,真是显得富丽堂皇。 东边村据传会看风水的一个人,那人我也认识,从二表哥的家门口路过,说:这个房子看着是好,就是不能住人,这个房子住着住着,就没人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一个周末,我有事去二表哥家,二表哥家满满一屋子村里整天不干正事的年轻人,烟雾缭绕,乱哄哄的在看录像,那时候还是磁带式的录像机,放的不知什么电影,不堪入目。当时我还想,风气实在太差了,这一家人要出事了。 没过多长时间,二表哥就离了婚。没过多长时间,二表哥又找了一个本村别人没结婚的媳妇,带着远走他乡。房子里没人住了,大姑姑去世以后,姑父从老宅子搬到这个房子,过了好几年。四五年前,姑父在公路上骑着自行车,被东边村的一个人骑着摩托车撞到,也没了。 现在,那个房子一直空着,没有人住。假期回老家时,偶然路过,那房子已经破败不堪,有的地方已经倒塌,早已不复往日富丽堂皇的模样。 #25.古怪的鸭子 本家一个堂弟,活着的话和我年龄差不多,我上高三时他已经参军。 高三那年夏天,高三的暑假也就放一个星期,就开始补课了。 一天,我正在上课,突然看见教室门口好像是父亲的身影经过,父亲不识字,很少出远门,我上了三年高中,算上送我入学,父亲总共到我就读的学校来过两次,第二次就是这一次。 我赶紧出去,果然是父亲。父亲正背着手在楼道里看上去似乎漫无目的闲逛,父亲找我的方式不是挨个教室问,而是在楼道里走,我觉得父亲当时可能想,多在楼道里走两趟,你反正能看见我。 我叫住他:大大(方言:父亲,爸爸),你来干么? 父亲看见我,不紧不慢的走回来。我和父亲一边往楼下走,父亲一边说:我到恁***家,您大爷二儿子淹死了,咱家族这不都过来坐坐,你跟我过去吧。 那位本家的大爷,就住在学校对过的大院。 我跟父亲到了大爷家,本就不大的小院子,被一棵葡萄树几乎遮住了一半,院子里显得很阴暗,很潮湿,很压抑,上午的阳光一丝都照不进这个院子。 大爷的头发像一篷杂草,他颓废的半躺在一个单人沙发上,虚扣着双手,闭着眼睛。我进门叫了一声大爷,大爷睁开眼看了下我,说了一句:你来了,便又闭上了眼睛。没看见大娘。 父亲是和本家的几个叔伯一起来的。大家都沉默地坐着,我也坐了一会,就悄悄的返回学校上课了,不知那天父亲什么时候走的。 周末回到老家,听说了那位堂弟淹死的奇异事情: 大爷的二儿子回家探亲,接着订婚。订完婚后的一天,和几个关系特别好的初中同学,一起去县城南边的一个水库划船,不知什么原因,船翻了,他和其他人落入水中,其他人穿的短袖裤衩,在水里很容易脱掉衣服游上岸。他那天穿着长袖上衣和裤子,还有刚订婚的女友送的新皮鞋。上衣系着袖口,很难脱掉,穿着衣服在水里游泳及其费劲,结果,他没能游上岸。 当天,本家的一位二哥帮忙去打捞,在水里没找到。第二天,还是没找到。 第三天一早,二哥他们一到岸边,一位放鸭子的老者告诉二哥他们,从昨天傍晚就出现了怪事,有几只鸭子在一片水里老是打转,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吸住了,游不出那片水域。老者说着指着那片水域给他们看,那里果然有四、五只鸭子在那里打转。他们一商量,去那里打捞试试看。到了那片水域,第一钩子就钩到了东西,拉上来一看,正是大爷的二儿子。 去年,我回老家,看见那位大爷,大爷已经痴呆,身上一股熏人的尿味。有人说,大爷是想那个二儿子想的神经失常。 当人遇到失去亲人的重大变故的时候,当时虽然悲痛,但是还是处于懵的状态,等着时间慢慢流逝,才会真正回过味来,那种无可名状、无法言语的锥心的痛,才会慢慢释放,没日没夜的折磨人,这种感觉,父亲去世后我有切身体会。可能大爷就是经受了这种折磨,才变得痴呆吧。 妻子的一位同事大姐,前几天不知因为对什么东西过敏,失去呼吸造成休克,时间长达二十分钟,医生说,大脑损伤极其严重。 医院看望,她还在急救室抢救。当时看她的儿子,很利落的跑前跑后,没看出什么担心、悲伤,据说她的儿子平时对她不是太好。可能那个儿子以为他妈妈经过一番抢救就会醒来,还会和正常人一样,每天上班,下班后给他洗衣做饭。 回来的路上我告诉妻子,那个儿子,这时候还没回过味来,过两天等他回过味来,他就哭去吧。 后来,妻子再去看望那位大姐,回来告诉我,大姐的儿子哭的跟泪人似的,说只要他妈妈能醒过来,哪怕不能动,能给他聊聊天他就满足了,等妈妈醒过来一定会好好孝顺的,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对待妈妈了。 看看身边的人,有的人就是犯贱,当拥有的时候,不懂得珍惜,等失去了,才知道珍贵,特别是夫妻之间。 大姑姑和大姑父两人经常因为一点小事打架,大姑姑经常被姑父打得遍体鳞伤。那年,大姑姑突然得了半身不遂,姑父一下子改变了度大姑姑的态度,端屎把尿,尽心尽力的伺候,说:只要有口气喘着,能陪着我就行。过了两年,大姑姑因病情加重去世。大姑姑刚去世的那段时间,大姑父经常一个人到山上大姑姑的坟头去哭。但是还有意义吗? 妻子的姐姐和姐夫现在也开始没完没了的打架,昨天晚上,妻子给我看她的姐姐被姐夫殴打的照片,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我想,这又是一对没活明白的人。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ibeichia.com/zbcsjfb/6307.html
- 上一篇文章: 清宫海错图海鲜你为什么那么萌
- 下一篇文章: 中国各省十大经典名菜,你知道几种吃过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