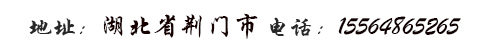那年,时光不老
|
北京哪家医院皮肤科 http://m.39.net/pf/a_4658077.html 紫贝拾遗 原创文章,欢迎转发,谢绝转载! 作者丨李浪 图片丨悉尼大学档案馆,邢艳 马尔克斯说:“幸福晚年的秘诀不过是与孤独签下不失尊严的协定罢了。”是的,她是与孤独签下了不失尊严的协定,可是她幸福吗?在那最后寂寂流逝的时光里,年年独自观望着蓝花楹的盛开、凋谢,枫叶从绿转黄,回忆着那不复再来的末日盛宴,揣测着不知尽头的归途。可是什么是幸福呢?如果说在那许多猝不及防的人生岔口,她能决然做出选择,改变她所能改变的,淡然接受她无能为力的,那又何尝不是种幸福呢? 一 悉尼Fairfield旧市政厅旁的街心公园。已是深秋,蓝花楹树刚泛着绿意,等待着十月的叶落花开;枫树摇曳着枯黄的枝叶,欣然接受季节的洗礼。早上九点半发黄的阳光下,匆匆走过手端咖啡的白领;一个妈妈佯追着蹒跚走路的幼儿,不时发出夸张的笑声。 她坐在长椅一角,黑色牛皮包挎在右手肘,眼定定盯着几只觅食的鸽子,嘴巴不时嚼动一下,如反刍的老牛。两片枫叶摇摇摆摆,如跳着最后的华尔兹舞,无声地飘落在她脚边,那里早已陈积了厚厚的一沓。 我和老彼走过去,叫声:二姑婆。她微微抬头,83岁的脸上仍很白净,没见一块斑点,一丝皱纹,桀傲的鼻子似乎不曾沾染沧桑岁月的苔痕,仍旧兀自高挺着,与老彼、老彼文昌乡下的父亲、泰国的爷爷如出一辄。一见我们,她瘪嘴一笑,叫声:老二啦。又说,每天只要不下雨,她都会在这坐上半天,看看人,看看鸟儿,不然整天一个人呆屋里,会神经错乱的。 她颤巍巍站起来,背似乎更驼了,齐胯的驼色大衣下是一笼越过膝盖的黑色中裙。此时微风吹起,她头上淡灰色的帆布帽子掉了,老彼帮她捡起戴上,她自嘲地笑了笑,说:“头发像你爷爷,快掉光了,不戴帽子难看。”老彼似乎文不对题地应着:“二姑婆要注意身体啊!” 她是我丈夫老彼的爷爷的妹妹。12岁时为躲避日本战乱,从海南文昌嫁到阿南(今越南)当童养媳。不久,因不堪忍受婆婆虐待,只身逃出,独自闯荡于南北各个城市,最终在西贡创下了自己的商业王国,显赫一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丈夫病逝,越共当权,她家所有家产被没收,随后和儿子流亡澳洲,老了孤寡一人,靠政府救济生活。 我挽着她的手走向她住的政府公屋。有些老人身上会有股馊味,那种你想躲又不敢躲的味道。她没有,很干净,散发着淡淡的玉兰花香味。那味道让人只想往她身上拱,贴着她,拥抱她。我知道,那是一款香奈儿香水味,我曾在她卧室梳妆台上见过,淡绿色圆瓶,中间有CHANEL标识。她总说:“吃用的东西要尽量选好的,钱不是靠省出来的!”这话二十几年前我就听老彼说过,虽然她12岁就离开文昌老家,虽然在接下来超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们几乎没有交集。 她住的政府公屋小区,有十几户人家,多数是当年越南难民。每户一室或两室一厅,各自连着二十几平方的后院。此时,空荡荡的停车场上,阳光恹恹,门前花圃,一只黄猫微咪着眼,悄无声息,仿佛时间停滞。 在幽暗的小厅,她用那浓浓的南洋乡音谈着过往,那是他们唯一能交流的语言。清晰标准的海南文昌话,只是不时夹杂些外来语,如法语、越南语、粤语、潮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台湾话。这些都是她能任意切换的语言频道,唯独不会英语和普通话。 二 那年,她刚12岁。娘说:“日本鬼子已下到村里,去海那边过更好的生活吧!”她以为,她只是到后海走走亲戚,避避风头。不曾想,这一去,和娘不止隔着后海的那片风树(木麻黄)林,还隔着汪洋大海,隔着近半个世纪的沉浮岁月;不曾想,这一去,那魂牵梦萦的家俨然是只知来向而无归途的所在;更不曾想,她的家乡——如那张第一次荣归故里时摄下的、她总随身携带的全家福一样,走过昏黄岁月但仍清晰如昨的家乡——不知何时已把她遗忘。 她隐约记得,当年跟随两个下南洋的人,不知经过多少昼夜的海上飘流,最后坐上一艘渡船穿过一条泥泞的河流。很久以后她才知道那叫湄公河,从此,她的人生便与一个叫阿南的国家扯上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她被带到一户人家。男孩对她很好。很多年后,当她再次遇到他时,他仍对当年的事心表遗憾。只是婆婆总对她恶语中伤,每天不是嫌饭煮硬了就是软了。在多次被无故扇巴掌后,她毅然逃到老乡家。开始只在餐馆打工,积累了小资金后,她租卡车到南北交战的山上倒卖木材。她说,当年的阿南,货源紧张,只要能进到货,在西贡至少能翻二三倍。只是这生意也是拿命拼的。有次她上山进货,在南北交界处的城墙上,赫然发现悬挂着七颗人头。 凭借原始积累,她开餐馆,进军房地产领域,一路所向披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她取得了法国啤酒南越总代理权。法国上好啤酒被源源不断运到西贡,卖给法国军队、上流社会。彼时,西贡几条最繁华的商业街上遍布她家房产铺面,做家事的工人、司机就十几个。 说起这段历史,她满脸洋溢着笑意,说:“那时生意真好啊!说来好笑,当年卖啤酒时,有个法国军官看上我。哈哈,我才不嫁给红毛鬼呢。也不知啥缘份嫁给了你昌公,他对我真好!不管我打麻将到多晚,都叫工人炖好燕窝等我回来吃。” 以为日子从此一路笙歌,一世安稳,岂料命运如此不堪。七十年代中,丈夫病逝,越共占领西贡,并以“资产国有化”为名掀起浩浩荡荡的排华风潮。她家所有房产铺面全数归公,四十多年心血毁于一旦。 顷刻之间,天地苍苍,无以家为。 入夜,当抢夺的喧嚣归于宁静,她从院子地下挖出一簸箕黄金——包括借给朋友和邻居的,按每人头缴纳12两给蛇头,带领亲朋邻里二十多口人,坐上了逃难的渡船,如四十多年前的历史重演一样,又一头扎进了太平洋漆黑的夜里。只是这更是一场生死未卜、前路渺茫的漂泊。在海上漂了近一个月,在数次被菲律宾,新加坡等港口拒绝后,终于停靠香港。一上岸,她便到一个制衣厂打工。她说,或许是此经历和她法国啤酒总代理的身份,他们很快获得国际难民署的接见。最后她和儿子选择了定居澳洲,其他人分散于美国和加拿大。 到澳洲后,儿子说要和朋友合伙做生意。她把暗藏于体内带出来的几颗钻石变卖给儿子做生意本。很快,血本无归。 十五年前,儿子说回阿南做生意赚大钱,一去不返。 “儿子是好孩子,只是交友不慎,娶的女人也不地道。”她说。 西贡沦陷前,她曾投资香港楼市,以亲戚名义。楼市高企时,亲戚私自把房产变卖,给两个儿子在美国买楼,全家移民。几年后,她才从外人口中得知,她在香港的投资已打水漂。 “啥就啥啦,就当送给他了,有什么办法呢。”她说。 时光斑驳叠错,老朋友日渐离去,唯有邻居阿南婆偶尔上门,还有门前日渐老去的黄猫。 当她淡淡谈起这一切,她说:“这一生,除了死,什么都经历过了。” 三 日子琐琐碎碎,再见到她时,已是四个月后。她很少打电话来,总说,知道你们忙,不便打搅。那天,她说:“我带你们去卡市吃海南文昌鸡,那里有家文昌鸡饭店味道和老家的很像。”如大多数海南文昌人,她喜欢吃鸡。虽然这肉质松垮的大种饲料鸡与大洋彼岸小村庄里逢年过节阖家举箸的那盘文昌鸡已大相径庭,但丝毫不影响她对鸡的挚爱。 卡市是悉尼著名越南人聚集区。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眼前晃动的、接踵而过的都是黑头发黑眼睛亚裔。商铺标着繁体汉字、越南语,耳边“嘎吾巴布”的越南口音英语,让人恍然置身于东南亚街头。 饭店在两街道交界处,门面已显陈旧,“MinhHO”的字号最后一个字母已褪个口子,如鼓足腮帮吹气的嘴。门口一棵大梧桐树,有鸟于巢,叽叽喳喳不绝于耳。 时侯尚早,店里空无一人,我们选个角落坐下。“文昌白斩鸡”很快上桌,皮黄肉嫩,蘸上酸辣爽口的姜蒜葱花酱汁,倒也如久旱逢甘雨一样,实实在在慰籍了肠胃。 她赞叹道:“这鸡煮的火候真好啊!以前我也很会做菜,但家里有两厨子,只有来重要客人时我才下厨。那年西贡警察局长和太太来家做客。我做红烧羊肉,羊肉用红腐乳腌过,放大料炒,香啊!那俩公婆下巴都快吃掉了。哈哈哈哈。” 她得意地笑着,声音清澈而悠远。忽地,她倏然顿住,眼神凝固,一脸迷茫的神情,仿佛在倾听着远方锅碗瓢盆、人声鼎沸的声音。 片刻,她说:“遗憾的是当年在阿南,有钱也不能往中国家里寄。两国不相往来,信都不让寄,否则要杀头的。后来寄给爹娘的钱,都是在澳洲餐馆打工挣的。我运气好,到哪都能碰到好人。那潮州老板看我干活麻利,每周多付我二十块。钱交税后,多数寄给娘了。我给钱她盖房子,还叫她在墟上买铺面。八三年回老家,和村里老小坐在门前庭院话家常。娘对大家说,我就靠这老二耙一耙就够吃了。” “哎,人生真快啊!也就短短几年,爹娘说没就没了。泰国老四说要是我一个人孤独就回文昌老家养老。可爹娘不在了,哪还有家啊?谁还记得咱呢?总不能指望侄子侄孙养着吧。哎,跨出家门,就再也回不去了。” “回不去啰,”她仍喃喃自语,“要是当年不离开家说不定就好了,如今啥都没有。” 她神情黯然,有种如青杏般酸涩的味道。我们不再说话,天地间一片寂静。 那刻,我想起村里的幼婆——这么叫她,是因为很长时间里她都是婆辈里最年轻的。男人很早“下南洋”去了丹麦,她14岁和一只公鸡拜堂,然后用余下70年时光守着这祭坛前的承诺,守着称之为“爹娘”的公婆,守着初一、十五周而复始的祭祀拜公,守着终归回来的“她的男人”。他七十五岁得了癌症,回来祭拜祖先,三个月后撒手人寰。 我想起村里老女人仍津津乐道的“德行”。在那贫瘠的年月,难得弄到点咸鱼肥肉,都是男人吃肉女人喝汤,即使是女人坐月子的时候。而女人生孩子,男人是不能去探视的,食物只能从窗户里远远递进去,因为女人生孩子的“污血”会扫了男人的好运。 我想起即便是今天,在那片响彻乡野尽出将军高官名人雅士的土地,从村到乡镇、到县城,穿越了上千年的封建迷信仍如铜墙铁壁一样深深掐陷在人们血肉里,且似乎将如那条古老的文昌河一样亘古不变。譬如一家的功劳都是男人的功劳,一家的霉运都是女人带来的;譬如生不出儿子都是衰女人的肚皮不争气;譬如男人以传宗接代为名,引以为荣的婚外生子……罄竹难穷。 如果——如果真的有如果的话——她当年不走,留在那海港边的小村庄,她的命运又将如何?如果她当年选择了法国男人而不是海南男人——嫁为偏房,那男人在老家已有原配妻子和四个子女,她后来作主把他们都接到西贡,在动乱中又帮助他们逃离到美国和加拿大,她的人生又会怎样?只是,人生犹如一场没有彩排就仓促上演的舞台戏,仅此一场演出,一个选择,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得知另一种选择的结局。 吃完饭送她回去,又见门前黄猫,蜷缩着身子,一动不动,仿佛时间凝滞。 她躬着腰站在门口,讪讪笑着说:“老二啊,有空常来啊。别太辛苦,人生几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 回去路上,老彼专注开着车,一脸严峻。曾经浓密乌黑的卷发这两年稀疏了许多,只剩薄薄一层直贴头皮。零星几根白发,如帆船点点,游离其中。 “时间好快啊!”我冷不丁冒了句。其实何止是她,每个人每天重复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生活,以为生命会像一架周而复始、永不停息转动的机器。以为时光不老,四季永恒轮回。殊不知,机器会随时损坏,或到其使用年限,而流年正泻泻而逝。而多少人如她,或早或晚,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究寂寞偿还。 四 一天傍晚,医院打来电话,她出了车祸,脚裸受伤,但执意不配合治疗。我们赶到手术室,只见她两眼紧闭躺着,手不停挥舞着不让人近前,口里直叫:“他们是坏人,是坏人,要杀人了,要杀人了。”四五个医生护士围在床边,束手无策。 我走过去,一只手紧紧拽住她双手——一双柔弱得如婴儿般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拍着她脸庞,贴着她耳朵,用只有我们彼此能听懂的语言,说:“二姑婆,侬是老二,不怕,不怕,他们是帮咱们的。你的脚受伤了,治好了又可以重新走路了。不怕哦。”她慢慢平静下来,医生给她打了针,她睡着了。 第二天再见到她时,她躺在床上,咯咯笑着说:“医院只让围了条袍子,裤子都不让穿,羞死人了。” 两周后,她推着助步车回家了。她打了很多电话给儿子,说:“儿啊,回来吧,妈去养老院只能等死了。” 儿子仍说等他赚多多的钱就回来看她。政府派一个阿南妹一周三次上门帮她做家务事,她说阿南妹每次来闲聊几句就走了。我们想投诉换人,她却说:“啥就啥啦,人家来挣点小钱,何必打破她饭碗呢。” 当晚,她摔倒在卧室,直接被送到了养老院。 养老院座落在离我们家四十多公里的郊外。她的屋子两人一室,邻床老妪,瘦骨嶙峋,不断呻吟着,声音此起彼伏,如深夜山谷里幽怨的夜莺。 她静静躺着,两眼望着天花板,一声不响。 护工推进午餐,几个小碗盛放着土豆泥、南瓜羹、牛肉泥、酸奶、苹果泥。老彼拿起南瓜羹,舀了一勺,递到她嘴边。她嘴巴微微张开半个勺子大的缝儿,老彼费力塞着,食物最终还是顺着嘴角流下来了。两周前,她还能说话时说,这里的食物都是流质,没有嚼劲,不好吃。 护工是个中年洋妇,圆嘟嘟的脸上布满温润的笑容。我对她说:“She’sagreatwoman(她是个很棒的女人)!虽然遭遇了很多不幸,却总是充满感恩地生活着。”护工说:“这些每天躺着无法言语的老人,乍看好像没有生活的气息,没有过去。感谢你们来了,我们才知道他们的故事。其实每个人都是唯一的,他们和外面任何人一样,都有着不一样、甚至更加精彩的故事。” 那晚,极少失眠的我彻夜难眠。我想起马尔克斯的话:“幸福晚年的秘诀不过是与孤独签下不失尊严的协定罢了。”是的,她是与孤独签下了不失尊严的协定,可是她幸福吗?在那最后寂寂流逝的时光里,年年独自观望着蓝花楹的盛开、凋谢,枫叶从绿转黄,回忆着那不复再来的末日盛宴,揣测着不知尽头的归途。可是什么是幸福呢?如果说在那许多猝不及防的人生岔口,她能决然做出选择,改变她所能改变的,淡然接受她无能为力的,那又何尝不是种幸福呢? 而每天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每个人内心又何尝离开孤独而存在?那幅蟒蛇吞食怪兽的图画,在外人看来只是顶帽子罢了。而谁又能透过箱壁看到小羊呢?或许只有来自外星的小王子吧。其实何止是她,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我们生命一隅。 五 下了整整一个月暴雨,闪电和雷声交织,狂风肆虐,枝叶横扫屋顶,街道洪流如柱。他们说,这是悉尼20年来狂风暴雨最疯狂的一个月。 暴雨和琐事牵绊,已三周没能去看她了。怀着内疚和不安,九月的周三午后,我们赶到她床边。她已形容枯槁,两颊深陷,眼珠发直,已辨不出原来的模样。老彼说:“二姑婆,侬是老二。”几分钟后,她两眼一合,头猝然倒向一边。老彼:“二姑婆睡着了。”那天,她再没有醒来。 迷途漫漫,终有一归。 几年以来,每次当我想到这终归要来的时刻,内心总是一片悚然。只是那天,当我把一大束百合花轻轻摆放在她棺木上时,内心却是安祥的,甚至有些释然,就如最后一次握着她的手,抚摸她的脸,默默和她说着最后的话:“回家了,回家了,你会再见到你的爹娘,你耙一耙就够他们吃了。耙累了,去搓回麻将,半夜回来昌公会端出温软的燕窝……” 在她住养老院的九个月期间,邻居阿南婆引领她入了天主教。神父和教友Kay时常拜访。那天,五十多个天主教徒聚集一堂,为她做了两小时弥撒,给她送行。 “她是热热闹闹走的。”我对老彼说。 在她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发现唯一一张照片,一张边角已泛黄的全家福黑白照:在文昌老家的祖屋前,济济一堂站满三排人,有五十多岁时的她、她爹娘、她兄弟、侄子侄孙,还有少年时的老彼。 那年,时光不老,她88岁。 作者:李浪年毕业于文昌中学,现居澳洲悉尼。虽淫浸洋文多年,人到中年,一日脑洞大开,自叹中国文字之美非洋文所及。故于闲暇之余,把玩中国文字游戏,自得其乐。 征稿启事 《紫贝拾遗》证明了乡土文学是可以在民间自发地萌芽、生长、开花、结果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乡土文化的兴盛远远不是一时、一人、一地的事情。要形成一个有利于乡土文学成长的氛围,既需要大量的作者持之以恒地写作和讨论,也需要大量的读者持之以恒地阅读和批评。 我们欢迎所有作者继续给《紫贝拾遗》编辑团队投稿。所有来稿都会经过“一稿、二稿、定稿”这样一个严格的审稿、修改和校对流程。被《紫贝拾遗》编辑团队接受的文章,首先会通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ibeichia.com/zbcjbxx/6316.html
- 上一篇文章: 抗癌中草药石菖蒲的传说与功效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