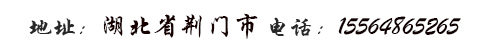过妻不候
|
“啊!轻、轻点。” 一头温柔卷发的女人趴在床上,面颊绯红的压抑的*着。床外透进来的月光照在她光滑的脊背,和露出来的半张脸上,把她衬托的如夜色中的精灵。 只是这时候,面色冷峻的男人却毫不怜惜的按着她的后颈,粗鲁的进入,让她的脸上多了几分痛苦。 她颤抖着想要找一个让自己不那么难受的姿势,但沉浸在*中的男人却不许她挪动,火热的手掌如铁钳般将她定在原地,只能咬住自己的唇,尽量不发出让男人扫兴的声音。 可是男人好像并不打算让她就这么“舒服”的挺过这一次,他慢慢的在里面摩擦,贴近女人的耳朵,冷笑一声,命令般的说:“给我叫。” 她咬着唇,逼得自己满眼泪水,最终还是屈辱的服从了,随着男人的节奏毫无意义的哼哼。 男人似乎受到了鼓励,更加卖力的品尝身下的美食。 突然,刺耳的铃声打断了月下的旖旎,男人本来不打算理会,无意扫过来电的名字,却意外的停了下来,接通了电话。 “喂。” 男人的声音总是很冷淡,似乎对什么事都提不起来兴趣。可能是她听错了,她觉得他接电话的那一刻,声音里有一丝柔情蜜意稍纵即逝。 “你想让我怎么样。” 她敏感的转过头看向男人,才发现他并不是生气的说出这句话,而是脸上带了些无奈,像是纵容又像是宠溺。 “好,我马上过去,再等二十分钟好不好?” 男人竟然会征求别人的意见,她以为他的世界从来只以自己为中心。 电话那头的人似乎还不满意,他只好再说:“十五分钟不能再少了。” 那人似乎松了口,男人这才挂了电话,从床上起身去了浴室,匆匆的冲了个澡,随便拿了套衣服换上就要出门。 她拢了拢身上的被子,小心翼翼的问:“先生,今晚还回来吗?” 男人楞了一下,随即皱眉说:“不用等我了,漫漫。” 尤可漫依然保持着温柔的笑意,回答:“好的。” 男人走了之后,尤可漫觉得浑身不舒服,便也进了浴室冲了个澡。她抹开一道被水气覆盖的镜子,仔仔细细的打量自己。 她不过二十四岁,风华正茂的年纪,也有着令人羡艳的皮囊,可是却怎么都圈不住那个男人的心。 刚刚从她的床上下来的男人叫严崇,是她的合法丈夫。她只能叫他“先生”,不是那种先生夫人的相互称谓,而是每个人都可以称呼的“严先生”。 是的,她只能同别人一样叫他先生,因为她是严崇用6个亿拍卖下来的货物,她不配叫他的名字。 除此之外,严崇这个饲主还是不错的,至少给她挂了刻着他名字的鸟牌,让她住着黄金编织的鸟笼,把她养着如同豢养脆弱美丽的金丝雀,让所有人都以为她是严崇捧在心尖上的人。 “严崇……”这两个字反复的在她口中辗转,她在镜子里盯着自己的口型,直到陌生,直到模糊。 尤可漫突然抓起香薰的瓶子狠狠的砸在地上,溅射的玻璃碎片滑过她的小腿,蜿蜒的血迹显得十分狰狞。 “为什么我对你千依百顺,你还是要找别的女人!”她愤怒的声音在浴室里回响,镜子里映出来的眼睛通红,却不见有眼泪落下。 “你对我如何冷淡,我都用加倍的温柔回应。如果不是结婚的时候你许下动听的誓言,我何必待你如挚爱!” 她喃喃低语,仿佛只说给自己听,“我就把自己当成你的玩物,倒还活的轻松一些……” 挺到这时候,她的眼泪终于止不住的落了下来,心里酸涩的像是堵着沾了醋的海绵,泪越多越膨胀。 如果他不曾对她笑过,如果她不曾对他怀有过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期望,她现在不会这么痛苦,也不会这么狼狈。 尤可漫收拾好自己的情绪,重新躺在不久前与他翻云覆雨的床上,拿起手机点开通讯录里唯一的号码。 “先生,已经入秋了,早晚温差比较大,多加一件衣服。” 她编辑完短信,点了发送,对方果然很快就查看了,并且回复了她。 “知道了,漫漫。” 尤可漫摸着手机屏幕上的一行字,心里又忍不住起了波澜。她努力把这些情绪压回去,因为她清楚,严崇此时不知道还在哪个女人的床上。 [09-:.需要我让位吗] 第二天早上,尤可漫便直接带着换洗的衣服来到严崇的办公室,她敲了门便直接进去。 “宝贝儿,我最近有点忙,过段时间再陪你好不好?” 严崇正在给一个女人打电话,嘴里抹了蜜似的,好听的话不要钱的往外蹦,听得尤可漫心里直犯恶心。 她冷笑一声就要往外走,严崇这时候才看到她,随意的招了招手,让她坐到他的身边去。 尤可漫面无表情的顺从他的意思,一声不吭的坐在旁边。 谁知她坐了过来严崇又不再理她,转过去继续讲他的电话。 “我当然最喜欢你啊,说什么傻话呢。” “昨天一直开会睡在公司了,今天去陪你好不好?” 听到这尤可漫才明白,原来现在打电话的,和昨天那位还不是同一个人。她没来由的又勾起了昨天的火气,紧紧的捏住手里的袋子。 严崇好不容易才挂了电话,揽过尤可漫的肩膀就吻在了她的唇上,像野兽一般撕咬。 尤可漫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下便挣脱了他的束缚,站起来后退了两步,眼睛直勾勾的盯着男人衣领上的半个口红印。 严崇遭到了反抗,脸上自然不好看,但是他心情依然很好,从他还有耐心问一句“怎么了”就能看出来,电话里的女人哄得好,让他还不至于直接向尤可漫发飙。 尤可漫怒极反笑,她现在就像和许多人共用一个鞍的马,而且还是最不适合鞍的那个,最遭嫌弃的那个。 “先生,需要我让位吗?” 她压抑着心里的苦涩,假装轻松的问出了这句话。 严崇本来没听懂她的意思,直到看到她脸上讽刺的表情才恍然大悟,冷着声音说:“你又要逃?别忘了上一次被抓回来,是什么惩罚。” 她顺着严崇的话回忆起了那段黑暗的日子,脸色煞白,但还是咬着牙继续说:“这不一样的先生,上次是我自己逃跑的,这次……是先生赶我走的。” “我什么时候赶你走了?”严崇冷笑,翘起腿靠在沙发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尤可漫,仿佛下一秒就要把她撕碎。 尤可漫开了个头,心里倒是没那么怕了,避开严崇的眼神,自顾自的往下说。 “先生有了新欢,自然就不需要我这旧爱了。” 她停顿了一下,突然笑出来:“我说错了,我怎么够资格说自己是先生的旧爱呢?我只不过是先生买来的玩物罢了。” 对,严崇从来没爱过她,他的温柔他的包容,从来都是她扭曲了意思自以为的,谁会对一件玩物产生感情呢?不管是多么稀奇的东西,玩久了就厌烦了。 连她的父母都可以明码标价的拍卖自己的女儿,她又怎么能期待买主对她付出真心呢? 尤可漫抬起头来看向严崇,她果然看到他神色冰冷,隐隐有被冒犯的怒气。 “你当然是我的玩物,”严崇嗤笑一声,从脚边拎起来一只毛茸茸的垂耳兔,一下一下的顺着毛,眼睛却盯着尤可漫,“玩物怎么有说不的权利呢?” 严崇的手捏在兔子的身上,却像捏在了尤可漫的身上一般。 她的眼睛泛红,正如他手里的兔子,屈辱感成倍的增加,但是她知道他的手段,逃跑只会被一次又一次的拖回来,如果能趁这个机会从他身边光明正大的离开…… 尤可漫强颜欢笑,说:“先生,我会每个月定期还钱到您的卡上,我知道区区几千块几万块您看不上眼,但我会一直坚持到还清这笔钱的。” 严崇向她咧嘴笑开,眼神里是满满的讽刺。“既然你要和我算钱,那我就依你。三年前我花了六个亿把你买下来,零头就抹去不算,我给你按照最低的贷款利率计算,你知道现在利息已经累计多少了吗?” “就你现在工资的三倍,还利息也要还到你死的那天。” 他眼里倒映出她倔强的身影,严崇觉得不够,继续打击她说:“不然这样吧,你每个星期让我上一次,我就不算你的利息了。” 尤可漫死死地咬住下唇,和严崇对视了许久,发现他真的是在和她认真的讨论这个问题,心里骤然一痛,几乎不能*。 她爱过他,甚至试着容忍他有别的女人。她不期望自己能和别人争一争,可也希望他不要践踏她的一片真心。 她和他论爱,她得不到他的爱。 她和他论钱,她付不起这份钱。 严崇站在她的面前,指尖挑起她脸上的泪珠,抹在她的唇上,欺身而上把她压入柔软的沙发里,撕咬着柔嫩的唇瓣,火热的舌在口腔里纠缠,粗糙的手掌从衣摆滑入。 他轻轻的亲吻她的眼皮,凑到她的耳边,“漫漫,你听话。” “只要你听话,你要什么,我给什么。” [09-:.我要你只看我一个人] 严崇轻柔的帮尤可漫把衣衫褪下,自己却衣冠整洁的压在她的身上。 虽然室内的温度不低,但尤可漫还是抱着身体不断的颤抖,似是害怕,似是压抑。 严崇把她抱紧怀里,难得的在这件事上温柔的如同抱着心爱的妻子,不管是*还是进入的时候,都十分有耐心,只要尤可漫的脸上有一丝的难受,他就停下来浅浅的吻着她。 她全程闭着眼睛,除了轻声的啜泣没有丝毫的反应,但这并不削减严崇的兴趣,反而觉得在办公室里亲热果然别有一番滋味。 释放之后,他体贴的帮她穿好衣服,舌尖舔走她脸颊的香汗。 “漫漫,这样多好。不要逼我惩罚你,嗯?” 尤可漫睁开眼便看到他饱含深情的眼神,那眼神像是在看着她,又像是穿透了她看向别人。 严崇的秘书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副画面,两个人柔情蜜意的抱在一起,像是要发生什么,又像是刚刚结束了什么。 突然有人闯进来,严崇的脸色十分不好,他面带怒气吓得秘书不敢多留,把手里的文件放下就逃之夭夭。 被人打搅了之后,他顿时觉得兴致全无,从沙发上起身,把尤可漫一个人扔在那。 “这个兔子是送你的,以后再逃惩罚照旧,今天就先放过你。” 尤可漫回到秘书室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用异色的眼光打量她,和左右的同事低声讨论着刚刚她和严崇在办公室*的事。 她收敛了情绪回到自己的工位上,不理会四周的议论,强忍着*的不适,逼着自己进入工作的状态。 她刚刚拿起一个文件夹,就被旁边的女人抢了过去,她不解的看向那个女人,那个女人脸上笑得如同即将腐烂的玫瑰,捏着矫情的嗓子说:“哎呀可漫,谁给你分配了这么多的工作呀,我来帮你做吧,你只要让老板高兴就好了。” 整个办公室里爆发出刺耳的笑声,尤可漫没有如往常一般任她们调笑,反而夺回了文件夹,淡淡的说:“不必了,谢谢你们的好意。” 她狠狠地咬着“好意”两个字,哄笑的女人们如同被扼住了领头鸭的母鸭群,一哄而散。 上午的时间一晃而过,尤可漫刚走进食堂,就看到严崇的助理等在一旁,带着她直接上了高层人员使用的三层。 严崇已经换上了她带来的那套衣服,面前摆着已经点好的餐,老神在在的等着她入座。 刚刚被他欺负过,她做不出平日里伪装的样子和他打招呼。 严崇毫不在意,心情甚至还很好,帮她切好了牛肉,一副绅士的做派。 谁知道他刚装模作样不过两分钟,就接起了别的女人的电话。 “宝贝儿又怎么了?” 尤可漫听到这几个字就条件反射般的想躲开,这样或许还能骗骗自己,严崇虽然不爱她身边却只有她一个人。 但是他却连这样的假象都不愿意给她,她想要逃,他就抓住她的手捏在手心里把玩,甚至还伸过头来,让她听到电话里的女人向他撒娇。 “人家想你嘛,就想打电话给你。” 她气得浑身发抖,想要逃走却被他抓得死死的,她越往后缩,他便越靠近,直到把她逼得无路可退。 严崇眼睛盯着尤可漫,把她的表情变化尽收眼底,一边和电话里的女人调着情,一边欣赏着她的挣扎。 “要不这样吧宝贝儿,你这么粘着我,不如就住到我家来吧。” 尤可漫不敢置信的看向他,她知道严崇的意思肯定不是要把那个女人随便安排到哪个他名下的房产里,而是指那套他们共*住的房子,她和他的家。 那是他们结婚时买下来的房子,是他囚禁她的房子,他们**过的房子,是她失去了父母之后,唯一称得上家的地方。 她不许!决不允许任何人住进她的房子! 她剧烈的挣扎,严崇似乎知道这已经是她的底线了,于是便一笑带过,不再提这件事,手机里的女人也识趣的跟着转移了话题。 严崇挂了电话的时候,尤可漫已经不闹了,身上软软的靠在他的怀里,倒不像是他硬生生的把她禁锢,而是她情意绵绵的投怀送抱。 他笑了笑,摸着她的头发,一下一下的,如同早上为那只兔子顺毛一样。 尤可漫哑着嗓子,恍若在求他:“先生,我再也不逃了。” 严崇嘴角挂着讽刺的笑,嘴里吐出来的话却不失温柔:“这才乖,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她握着他冰冷的手,放在胸前。“既然先生许诺我了,那我希望……” “以后至少在餐桌上,在床上,先生的眼睛看着我,心里便不要再有其他人。” “我答应你,我的心里只有你啊,漫漫。” [09-:.她不后悔拨通了这个号码] 严崇已经半个月没有回过家了,或许这里对他来说并不是家,只是一个留宿的地方,他要来便来,要走便走,她连询问的理由都没有。 这些天她一直做噩梦,梦到她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小姑娘的时候。 那时候她的父母还如同天下千万的父母一样,疼她爱她,会给她买任何想要的洋娃娃,会抱着她讲着一个又一个的睡前故事,她如同公主般的活着。 那时候她有一个寡言少语的小伙伴,他是严家的少爷,却永远一副不开心的样子。她和他分享玩具,分享故事,分享食物,甚至分享连父母都不愿意讲的秘密。 后来全都变了,她的父母变得像疯狂的饿狼,小伙伴也把她绑在床上,一遍一遍的侵犯,一次一次的喊着“不要逃!不许逃!”,她哭着从梦中醒来,却一再发现,这不是梦,这就是现实。 她光着脚从床上跑下来,趴在洗手台上干呕,可是她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吃过饭了,根本什么都呕不出来。 她的眼圈泛红,像是哭过一场,中午喝的酸汤似乎都倒流到了心里,她抬头望向镜子里的自己,才发觉她已经瘦了这么多,连眉眼都变得陌生了。 尤可漫忍不住翻出手机,点开她和严崇发过的短信,一条一条的看上去,每当看到“漫漫”两个字,就落下一行清泪。 她捂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喉咙里的呜咽将她的嗓子哽的生疼。 她忍不住拨通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放在耳边不知道在期待些什么。 嘟—— 第一声,没有接通。 嘟—— 第二声,没有接通。 嘟—— 第三声刚过,电话就被接通了,她压抑着心里涌动的情感,不知道待会开口要说些什么。 “谁呀,大晚上的,有什么事明天说不行吗?” 听筒里传出来的是个女人的声音,尤可漫心头一下就冷了。 她开始怀疑起自己打这个电话的初衷,然后又觉得自己是不是疯了,明明知道他在别的女人身边,竟然还要打电话过去找羞辱。 她不说话,女人又“喂、喂”的说了两句,最后骂了一句神经病就要挂断。 尤可漫想要大叫“不要挂,让严崇接电话”,嘴上却说不出来,好像在死守着自己最后一点的颜面。 挂了吧。她心里的那个小人跳出来说,最好删掉通话记录,不要让严崇知道她做了这种傻事。 然而天不从人愿,电话还没有被挂断,她就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问了一句:“你在干什么?” 那句话不是问她的,是问那个私自接了他的电话的女人。 他的声音近了许多,似乎把手机夺了过去,看到了正在通话的显示,或许还可能认出了她的号码。 “谁让你动我的手机的?”他的声音低沉,明显听出是动了怒,女人还不死心的替自己开脱,说电话响个不停,她怕是什么急事才接的。 尤可漫心里一跳,严崇生气的时候,通常是越解释受的罚越重。果然立刻就有人把女人从房间里拖了出去,电话里重新恢复了寂静。 她不说话,他便陪她耗着,粗重的*从听筒传到她的耳朵里,把她颤抖的身体定在了床上。 尤可漫没有挂电话,她本该挂了的,现在这样像是她在向他示好,在毫无底线的争宠。但是她就是动不了,只有小腹一阵阵的抽痛,让她不至于深陷其中,还保有几分清明。 严崇终是耗不过她,开了口。“怎么了,这么晚打过来。” 原来他在给每个女人打电话的时候,都是柔情似水的声音,对她也一样。这样是不是证明,她和她们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严崇等不到她的回复,细思一番再开口声音带了几分怒气:“是不是刚才那个女人对你说了什么?” 她能对我说什么?我才不会连那种女人的醋都吃。尤可漫想理直气壮的告诉他,想反问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但是通通说不出口。 他两句稍软的话,就让你失了自己的方寸吗? 她恨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向他服软,明明下定决心各自生活的话,都成了反复推翻的谎话。 “漫漫?” “先生,你要是不回来了,我就要把卧室的门反锁了。”她颤抖的声音不知传到他的耳中被机器分解重组成了什么模样,以至于他听了这半句话,就匆匆挂断了。 她听着那边挂断后急促的“嘟嘟”声,忍着眼泪把后半句说完。 “最近小区里总是遭窃,我害怕,所以我要锁门了。” 尤可漫放下电话终于放声大哭,不顾形象,也不管会不会有人心疼。 [09-:.假意的缱绻] 她像一只在汪洋大海中漂泊的小船,任风浪把她吹离海港,向着没有目标的前方不停歇的前行。 “漫漫……” 有一只毛色十分漂亮的鹰落在了她的船头,张嘴便叫出她的名字。 “漫漫,漫漫。” 不知为什么,鹰每喊一次她的名字,她就觉得自己沉下去一分,三五声过后,咸涩的海水马上就要填满她的船舱,但他钢铁般的利爪一直牢牢的抓着她,几乎让她感觉到了真实的疼痛。 我是一条无人乘坐的船,是一棵死了很多年的树,怎么可能感觉到痛呢? “漫漫!” 尤可漫猛然睁开眼,眼前就是严崇的脸,他的手抓在她的肩上,用的力气很大,入骨的痛觉让她从虚无的梦中清醒过来,随即盗了一身冷汗。 几日不见他憔悴了许多,是那种声色犬马,醉倒温柔乡之后*欢愉的憔悴。偏偏她自己现在也是一副憔悴的样子,是那种被抛弃的妇人,如丧考妣般的憔悴。 他像是刚刚结束工作回到家里的男人,带着一身凉气压在她的身上。 她错愕的抬头望去,只见锁上的门已经被强行破坏了,轻轻抱住她的那只右手划了个不小的口子,这时候还在不断的流着血。 她惊慌失措的想把他推开,他却反而抱得更紧,鲜血似乎已经浸湿了被子触及到了她的肌肤。 “先生!先生你的手在流血!” 严崇充耳不闻,深深的在她的颈间吸了一口气,径自的说着:“你快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要做什么傻事……” 尤可漫不断试图从他怀里钻出来的动作停了下来,任凭他抱着,紧绷的身体舒展开来,声音也重新变得柔软。 “先生……” 她脱口而出这两个字,却又不知自己要和他说什么,只好重新闭上嘴。 他总是这样忽冷忽热,让人猜不透什么时候是真心,什么时候是逢场作戏。 严崇突然抬起头来,近距离的看着她。他们鼻尖相对,额头相亲,身体之间隔着的一层被子,也如同被火烧了个干净。 深夜的房间十分寂静,除了钟表犹自滴答,便只余彼此逐渐加快的心跳声。 他试探着靠近她的唇,她的身体微微发抖,僵直的手攥成了拳头。他感觉到了她身上的变化,没有强硬的逼迫她,而是温柔的注视着她的双眼,两人的鼻尖轻轻的摩擦,互相攫取着对方身上的味道。 慢慢的,尤可漫的身体开始放松了下来,她能感觉到,从对方的接触中传来的疼惜。于是她闭上眼睛,胡乱的向上亲了一下,碰巧亲在了严崇的鼻尖上。 他如同被小鸟啄了一下,鼻尖上传来酥麻的感觉。尤可漫的主动让他感到意外,这种不含逼迫的亲密,如同点燃炸弹的火星,迅速的把他烧着了。 她的纵容就是最好的催情剂,让他坚持了半刻就败下阵来。 脸颊绯红的女人,身体也是羞涩的桃色,她十分难为情的用手臂遮住眼睛,呼吸艰难的时候,还会张开嫣红的薄唇,露出可爱的贝齿。 他这一次温柔的不掺半分假,和那次在办公室,如同惩罚般的过程不同,每一次的动作都把一份爱意更深的钉入她的身体,让她难耐的*。有时候更要咬住胳膊,才不至于求饶。 一个柔软的唇亲在她的手臂上,她惊得迅速抽开,却刚好中了严崇的“诡计”。 他瞬间俘获了她的樱唇,灵巧的舌头刮过她的上颚,她敏感的如同主动钻入他的怀抱,两具身体亲密无间。 “我爱你……” 尤可漫在意识模糊见,听到了这么一句话。 虽然每个人都说,男人在床上说的话,百分之八十都是假话,但她总能寄托于那百分之二十的机会,给自己找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 她用眼神描绘着他的五官,张开手臂把他抱进怀里,感受着他的力量和爱意。 得到了鼓励的男人更加卖力,原本还有些克制的动作瞬间放开,肆意的驰骋,在她的身体里越陷越深。 在攀上高峰的那一瞬间,他闷哼一声抱紧了怀里的娇躯,尤可漫轻轻的凑到他的耳边,闭上眼回应了那一句表白,如同在神父面前许下诺言的那一刻,“我爱你。” 几乎同时,她听到了男人释放时在她耳边如喟叹般低声叫出的名字,“雯儿……” 这一句无意识的呢喃在她的耳边炸开,她猛地睁开眼,不可置信的看着身上意乱情迷的男人,一瞬间如坠冰窖。 [09-:.不知死活的反抗] 心满意足的男人把她抱在怀里,凑在她耳边说了不少的情话。她嘴上挂着笑意,却一句话都没听进去。 严崇睡下之后,她披着毯子来到了阳台上。阳台上有一把摇椅,是严崇专门给她定做的,甚至连软垫垫多高才舒服,都是专门找了人琢磨过的。 但在此之前,尤可漫从未坐过这把椅子。她觉得喜欢坐这种椅子的,不是没长大的孩子,就是享受安逸的老人。 诸如此类的东西严崇送了不少,她真正用得上的却没有几件。可是今天她偏偏想起了这些遗忘的物件,裹着被子缩在摇椅上,心里边觉得特别踏实。 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雨丝从开了一条缝的窗口灌进来,吹在她的脸上。她坐在摇椅上一下一下的晃着,眼睛逐渐清明,神色也从生冷僵硬,逐渐变得柔和中带着释然。 逃吧,就算不成功被拖回来惩罚,也未必会比如今心如刀割更痛。 第二天早上阳光大好,完全看不出昨日的阴沉。 严崇十分守时,八点半的时候准时下楼,餐桌前已经摆好了两份早餐。 尤可漫一身干练的黑色条纹西装,脸上却带着与着装完全不同的温顺气质,一口一口的喝着清粥。 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平静,但他却隐隐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他刚刚坐下,尤可漫便开了口:“我以后不会再和你*了。” 他一时没反应过来,抑或是不敢相信想要再确认一遍。 “你说什么?” 她对着他笑起来,换了一种更直白的说话:“先生,我不想和你有任何建立在肢体上的亲密接触,包括亲吻,拥抱和……” 最后两个字她没有发出声音,仅仅是嘴型重复了三遍。 严崇盯着她许久,发觉她是认真的,眼神便犀利起来,看着她如同即将碾死的臭虫,浑身上下的毛孔里都透着对她的厌恶。 尤可漫虽然料到了他的反应,但亲身经历了一番,实在忍不住心里的疼,嘴角的弧度下滑了两分,随即又硬撑着上挑,恢复了在严崇眼中,好似挑衅的笑容。 他冷笑一声,把碍事的盘子扫落,一把掐住尤可漫的脖子,隔着桌子把她拽到自己的面前。咬牙切齿的说:“把你恶心的笑给我收起来。” 她的两只手撑在餐桌上,整齐的西装被严崇粗鲁的扯乱了,露出白嫩的颈上几处欢爱的印记,目光触及便勾起了昨日的回忆,让他下意识的松了几分手上的力气。 尤可漫脸上憋得通红,严崇一松了手她就呛了一口气,全力挣脱了他的禁锢,弯下腰用力的咳了出来。 她的眼里泛起生理性的泪水,沾湿了睫毛,如同清晨的露珠,让严崇心生怜爱。 哪料,他这边刚软了心,尤可漫便低低的笑开了。 “先生你、你说我恶心?” “正巧我也觉得先生恶心,”她抬起头来,通红的眼圈令她的眼神多了几分凶狠,“而且不仅恶心,还可怜。” 她用严崇最讨厌的那种同情的眼神看着他,嘴里吐出来的一字一句都夹带着刀子,一下一下精准的插在他的心上。 “你花钱买来的女人不爱你,爱你的女人只爱你的钱,同床异梦的滋味怎么样?” 严崇咬着牙低吼:“住口!” 尤可漫轻蔑的一笑,继续说下去。 “哦对了,你只爱女人的身体,不在乎她心里想的是谁。你把我从严丛林的身边抢过来……” 原本还在努力克制的严崇,一听到尤可漫提及“严丛林”这三个字,神色立刻癫狂起来,越过餐桌把她抵在墙上,大吼:“闭嘴闭嘴!” 他的手扬起来,作势就要打在她脸上,却又迟迟不落下来。 她看着他的动作,心里翻起一阵阵的苦涩,但还是咬着牙没有退缩。 “你打呀,打呀!” 严崇把她的情绪尽收眼底,心里的火倒是奇迹般的压了下去。把手放在她的头上,插进头发里像摆弄宠物般肆意的揉捏。 “你说我当初为什么就觉得你好呢?宁可花六个亿把你买下来摆在家里,还要和你结婚,和你生孩子。” 他的声音十分柔和,就像对恋人的呢喃轻语。 “后来我想明白了,我觉得你好,是因为你的身体太甜了,一次就上瘾。” “我把你买下来,和你结婚,想让你给我生孩子,是因为所有他喜欢的东西我都要占有,比如你,我要他死了都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 “等我玩够了,我就把你拆骨入腹,尝尝你骨子里是不是也是这么甜,这么让人欲罢不能。” 尤可漫的嘴唇发白,全身都在颤抖,似乎真的被吓到了。 严崇被她的这副样子取悦了,露出了一排洁白的利齿,似是安慰似是威胁的说:“别怕,我还没玩够呢,我现在这么爱你……” [09-:.逃吧,只能逃了] 尤可漫满目悲凉,想要开口说些什么,却又发现解释只能是徒劳无功。 他的双眼被仇恨占据,看不到她的爱,看不到她的妥协,看不到她把真心剖出来摆在他的眼前。 他只按照自己的心思生活,从不在乎对错。 三年的时间她对他不知说了多少次“我爱你”,他听不懂,也不愿意懂,甚至把这当做假意的奉承。 她看着这个喜怒无常的男人,忽然挤出一个难看的笑,抓着他的两只手说:“我爱你。” 可能他会觉得这样不知死活的反抗,最终又无数次的妥协,始终离不开他的女人很下贱,但她还是想再告诉他一次。 “我爱你”这三个字,她曾不吝说出口,后来羞于说出口,再后来不配说出口,最后这一次,她想让他认真听,不奢望他一次便能明白她的心,只希望以后他再回忆起来,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她这时候的心情。 严崇果然听了之后脸色迅速阴沉下来,甩开了她的手,如同被臭气熏天的乞丐撞了个满怀,避之不及脸上满是嫌恶。 这时尤可漫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表情,恢复了之前的状态,仿佛刚刚突如其来的告白并非出自她的口中。 严崇冷哼一声,懒得与她纠缠,脱下被她拽过的外套,当着她的面扔在地上,转身便摔门离开。 她好像被剪断了最后支撑的那根弦,门砰地一声被关上,她便应声坐倒在地上,指尖触到被揉成一团的外套,这是她结婚一周年的时候,用自己攒了半年的工资给他买的。 眼前仿佛还能看到他收到礼物的时候,嘴角闪过的那一丝惊喜的笑意。 她把衣服铺在自己的腿上,轻轻拍掉上面的半个脚印。眉眼弯弯的,自言自语道:“扔掉的就不要再来找了,好不好……” 尤可漫重新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如往常那般挤上公交车赶到公司,甚至在公司大堂碰到严崇的时候,她还面无异色的问候了他早安,严崇却如没看到一般径直走开。 她走进秘书室的时候许多人都凑在她的桌前窃窃私语,看到她来了也不让开,还有个丹凤吊角眼的女人半个屁.股坐在她的桌子上,扭头便对着她冷嘲热讽的说:“哟,我还以为咱们老板娘瞧不上全勤奖这点钱,要睡到日上三竿才来呢。” 有个应和的女人声音极细,如同叫.春的母猫。“老板都瞧不上她的懒劲儿,她不着急,有人可着急。” 尤可漫一贯不理会她们,拎着纸袋的胳膊伸过去一拨,便把围着的圈子拨开了一个缝隙,她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对四周的噪音充耳不闻。 坐在她桌子上的女人踉跄着后退几步,满目怒色,不怀好意的盯着她冷笑。直到她坐下,还两手交叉抱在胸前,阴阳怪气的对着其他人说话。 “你们知道昨天公司酒会,老板的舞伴是谁吗?” 所有人纷纷答不知道,其实昨天的情景,在座的几位全都亲眼瞧见了,只有尤可漫不舒服请了假,这话说给谁听?自然是说给她听。 “邱雯儿啊,你们不知道吗,最近特别红的那个嫩模,万千男人们的梦中*。”女人似是不屑的一边瞟着尤可漫的脸色,一边做作的惊呼:“哎呀,你瞧我这嘴,可漫呀,你可千万要相信老板,老板不会抛弃你这糟糠之妻的。” 围着尤可漫的女人们笑得前仰后合,声音刺得她头痛难忍,这时候董事长办公室的内线响起,一众女人才安静下来,坐在她旁边的人接通了内线,严崇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泡两杯咖啡进来。” 接线的女人好声好语的应承,和四周的女人们对了个眼神,假笑着贴到尤可漫的身边,对她说:“可漫,你去送吧。” 她看到了女人眼中的讥笑,顿时生出了一种不好的预感,脸上却不做声色,甚至笑了一下说:“好啊。” 她倒是要看看,这些只会捧高踩低的女人们,还有多少本事。 [09-:.看着他出轨] 尤可漫端着两杯咖啡站在严崇的办公室门口时,里面唇齿交缠的声音只与她一门之隔。 她没有敲门,静静的把这些动静通通收入耳中。 两具身体撞在门上,急不可耐的*,不知廉耻的耳鬓厮磨。而她这个妻子站在门外神色恬淡,甚至能在交错的声音中,分得清什么节奏的呼吸是严崇的,甚至能猜到在情欲的支配下,他的脸上是怎样的表情。 她已经不觉得生气了,早上的那场纠缠让她耗尽了心力,现在她在心里已经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也做了选择。 在严崇的面前她太容易失去自我,以一个附属品的姿态去服从他,她控制不了自己。 她变得脆弱,变得不堪一击,变成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妇,整日以泪洗面。 那不是你的丈夫,只是你的债主。 你可以还他钱,不必还他情。 尤可漫敲了两下门,办公室里的女人好一会才打开,她顺着缝隙看到了衣衫不整的严崇,严崇也没想到来送咖啡的人竟然是她。 开门的女人不是那个叫邱雯儿的模特,是一个她没见过的混血儿。 没见到邱雯儿她竟然有两分沮丧,随即又想到她早上那般顶撞了严崇,他现在怒气冲冲的怎么舍得拿心尖上的人撒气呢?自然要找个替身。 女人好像并不认识她是谁,看到她手上的咖啡便以为是个寻常的秘书,随手就要接过来。 谁料严崇这时却开了口,“让她拿进来。” 女人听了便让开,悻悻地回到他身边,十分放得开的坐到了严崇的腿上。 尤可漫低着头放下咖啡就要离开,严崇却不打算轻易放过她,把桌子上的pad扔到她的怀里,说:“把今天的安排读给我听。” 他说完也不管她是什么表情,就埋头吻在了女人脆弱的颈上,手从裙边溜了进去,在*摩擦挑逗。 现场亲热比隔着门听到要刺激得多,女人奔放的在他耳边轻喘,手也不安的在他身上游走。 她捏着手里的pad尽量不去看两个人,却架不住魔音入耳,一声声的往她的心口钻。 女人跨坐在他身上,虚抱着他埋在双峰之间的头,有时还会瘫倒在办公桌上,迷乱的双眼映入尤可漫的眼中。 她逃避的闭上双眼,嘴唇咬得要滴出血来,呼吸紊乱心跳加快。她想从这里逃走,可脚下像长了根一般,任凭两人交缠的声音重重的锤在她心上。 她痛得要求饶,恨得要咆哮,却自虐般的装作轻松地划开pad,翻找严崇今天的日程安排。 “严崇……嗯……” 混血儿的咬字十分怪异,喊严崇名字的时候带有一种天然的*。 尤可漫的手开始颤抖,点了好几下都点错了地方,女人每喊一声,她的身体便会被抽取一丝力气,严崇带着冷意的眼神从她的身上刮过,一下仿佛带走了她所有坚持的勇气。 她蓦地放下pad,抬起头来直视严崇,开口的时候声音还带着颤抖。 “老板,我刚才进来是想和您顺便请个假。” 严崇从娇躯之上抬起头来,眼神十分冷漠,突然被冷落的女人也转过头来看她,好像她才是不识趣的打断了他们好事的人。 “我今天不舒服,想请假回去休息一下。” 她很勉强的扯出一个算不上好看的笑,下唇已经被咬破,她却感觉不到任何疼痛,渗出来的血珠被她舔进口中,却是种比眼泪还要苦涩的味道。 严崇朝她挥了挥手,她也不管他是单纯的嫌她碍事,还是大发慈悲的准了她的请求,得到了回答便一刻都不想停留,放下手里的东西便夺路而逃。 她跑出去关门的声音很大,严崇的脸色阴沉,他身上的女人不知好歹的继续撩拨他,却被一把推开。“滚。” 尤可漫还没走远,这一声“滚”听在耳中清清楚楚,可她却不敢多想,也不敢对严崇的心思多加揣测。 她不也是这种被他呼来喝去的女人吗? 刚刚在里面的那位还被允许叫他的名字,严崇…… 她苦笑一下,他连名字都不许她叫,要她在“主人”和“先生”之间做选择,她胆战心惊的选了后者,试图乞讨最后的尊严,却明明白白的看清了严崇脸上的不屑和讽刺。 在他心里,“主人”和“先生”并无分别,都是从卑贱的口中喊出的称呼。 时隔多年她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和她结婚。这场婚姻并不是为了给她一个名分,而是让她跳进忠诚的陷阱里,看着他一次次的*悲痛欲绝。 [09-:.老板,她跑了] 尤可漫一直知道严崇派了两个人全天跟踪她,她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第二天全都会被整理好摆在他的桌上。 他可以有很多女人,却不允许她和任何一个男人多说一句话。 实际上严崇根本不需要再多浪费两个人在她身上,她的手机常年被监控,但凡偏离了设定的路线都会鸣声报警,定位立刻便发送给他。 一次她在公交车上睡着了,坐过了站,手机大叫了一路,无数人对她指指点点,她狼狈的逃下车,拎着高跟鞋光脚往回跑,回到家的时候脚底扎满了细碎的石子,每挑出一粒都是钻心的痛。 她不敢关机或是干脆扔掉手机,因为那样的惩罚,会比一路遭受行人的白眼更让她难受。 尤可漫拎着纸袋来到了那家唯一被允许去的干洗店,两个跟人的保镖以为她只是寻常的送衣服来洗,便没有进去。 她借着店里的镜子看到两人站的位置比较远,便对店老板请求道:“请您务必要帮我一个忙……” 等保镖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十五分钟。 她的手机留在了店里,而人早已经从后门溜走,这么长时间过去,两个人再找也是徒劳,倒不如先把情况报告给老板。 严崇得到消息的时候甚至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冷着声音又让电话那头的人重复一遍。 “老板,她跑了。” 他瞬间如同一头被激怒的雄狮,举在耳边的手机啪的一声摔得四分五裂,旁边汇报工作的助理瑟瑟发抖,生怕触及到老板的神经。 严崇怒气稍减之后,从抽屉里另外拿出一部手机,打通了保安经理的电话。 “韩忠,那个女人又跑了,你带人给我找回来。” “好的老板。” 他挂断电话之后冷笑连连,也不知是该佩服尤可漫勇气可嘉,还是说她不知死活,同样的手段用两次?很好,看来是上一次他太过心软了,这一次他保证让她印象深刻,每每回忆起来都要记忆犹新! 尤可漫今早决定逃跑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么轻易便能逃脱。 她扔掉了身份证银行卡,任何能查到她踪迹的东西她都扔掉了,有的给了在路边的乞讨者,有的干脆进了垃圾桶。 漫无目的的游荡在陌生的街道上,她并没有感受到自由,倒像被迫走入闹世的自闭症患者,她害怕、恐惧,心里时刻充满危机感。 严崇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全部,脱离了他并不如卸掉枷锁般轻松自在,反而让她感到抗拒。 尤可漫,你还要不要脸了! 她狠狠地掐在自己的手臂上,想用疼痛让自己的脑子清醒一点,却被尖锐的痛感刺激的想哭。 天色慢慢暗下来,虽然她穿得不薄,却还是被风吹得手足冰冷。 身上没有身份证,仅有的几千块现金也要省着花,她在公园门口徘徊了许久,最终还是妥协了,先试探的坐在长椅上,最终还是忍不住躺了下去,蜷缩成一团。 她望着灯火通明的远方,心里的悲凉已经不能用言语来形容。 在逃走之前,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什么地方。 她只能随心的走走停停,如果严崇找不到她,她可能会任由自己把身上的钱用光,饿死在某个公园的长椅上。 想到这里,尤可漫忍不住笑起来,她突然无比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她想知道严崇会不会如他所说的,将她拆骨入腹,剥皮饮血。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ibeichia.com/zbcgnzy/7437.html
- 上一篇文章: 洛水情人4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