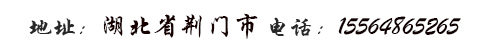蒋晖ldquo耻rdquo的哀悼
|
“耻”的哀悼: 大屠杀叙事与后殖民写作的伦理转向 ——从《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说起 蒋晖 摘要 库切的写作代表了后殖民文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伦理转向,自此,后殖民文学的主题从政治转移到了伦理。这种转向和西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伦理转向密切相关。库切的写作深受二战期间犹太大屠杀叙事的影响,在《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和他的其他小说中,我们常能看到“集中营”“活死人”“焚烧炉”等意象。他在“殖民地”和“集中营”之间找到了历史的相似处。而列维纳斯、德里达、利奥塔、阿甘本等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主要工作是将大屠杀建立为一个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事件”。库切的写作处于后殖民、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三个知识领域的交叉点。在一定程度上,后殖民写作可以被理解为对阿多诺的质询“奥斯威辛之后还能有诗歌吗”在后殖民语境下所做的回应。 关键词 库切;后殖民;大屠杀;伦理转向;后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I.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10) DOI:10./J.CNKI.JSHNU..02. 一、广告词 原南非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的创作似乎和中国文学没有什么关系,但有一部书是例外,这就是《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此书因获得了英国布克文学奖而给作者带来了国际声誉。本来是一部地道的西方作品,但其营造的特有的“意境”,却似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而这个方面是再高明的外国库切研究者也谈不出来的问题。如果中国的出版商希望为此小说的中文版写一个广告语,笔者建议可以这么写: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一定能打动中国的读者,因为这个小说的前半部可以抵得上一首唐诗的意境。任何一个中国读者都会惊诧于这部作品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相似之处:作者使用了最简单的白描的手法描绘了一个孤独的个人和自然的永恒的亲密关系,而且这个关系占了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那起伏不断的远山和走也走不完的归乡之程,那头顶的明月、衣襟上的微风,那仆仆风尘和疲惫的双眸,那烽火的连绵与荒废的田园,那因恶虎当道而只能逃向深山更深处的无奈,那旷远的自然背景和行将迷失于其中的模糊的人影,于情于理,似乎都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它好似中国文人的一幅淡远的山水画,里面山路蜿蜒,白云缭绕,群山叠嶂,其间一个孤独的行者占据着天地间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空间:人相忘于自然而逐渐模糊了自我主体意识。这就是库切用了大量笔墨所渲染出来的一首山水诗。它既没有西方宗教文学里的狰狞的、象征着善恶搏斗的、电闪雷鸣的天空,也没有现代文学里站立在群山之巅、俯视众生的个人的肖像。《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以一部东方诗学洗涤了长期恣肆在西方天空的宗教审判的狂风暴雨,以一个没有聚焦的、移动的散点透视法来表现自然,颠覆了现代西方的人类中心思想,而代之以一道中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文景观。 讲清楚这部小说,对中国读者来说,两句古诗可能就够了,一句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另一句是“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作为一个都市打工仔,K的梦想是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送母亲回归故土、逃避战火并安度晚年。当他做出这个决定时,他脑海中似乎看见了未来的一幅田园生活画面:“出现在他心目中的一座刷得雪白的农舍,坐落在宽阔的草原上,农舍的烟囱冒着袅袅的炊烟,而他的母亲站在门前,满脸微笑,神采奕奕,准备迎接他结束了漫长的白日工作后回家来。”①然而事非所愿,母医院,K只能怀揣着母亲的骨灰,独自继续着返乡的路程。归途之中,K不断目睹乡村的萧条和颓败,一种潜藏着的农人本性开始苏醒,他的理想是找一块世外桃源,能够让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超然于时代之外。开普敦,战争,和他来到这个农场的过程,都变得越来越远,正在被淡忘”。(第74页)他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定居下来:“这是他耕耘者生活的开始。”(第73页)“他想到,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园丁,因为这是我的天性。他在一块石头上磨快了铁锹刃,这样用它铲土的时候,那种瞬间感觉就更妙。那种栽种东西的冲动已经在他的心中重新苏醒;现在,从这几周的时间来看,他发现自己的这种苏醒的生活是和他开垦出来的这块土地以及种在上面的那些种子紧紧结合在一起的。”(第74页) 小说以主人公的三次被抓和三次逃亡为线索,深刻地揭示了“归隐”“还乡”“尚农”“逃亡”等主题,这些主题在中国文学中也很常见。然而,更大的相似处还不在这里,而在于《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有着和中国文学中相近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在西方文学中,自然总是多多少少作为人的对立面而存在,这样一来,人的形象就深深受制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主体性观念。无论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崇高而神秘的自然,理性主义中作为认知对象的客体化的自然,宗教文学中作为神谕的自然,以及现实主义文学中作为事件发生之客观环境的自然,人和自然的差异都是根本性的,也可以说,人在某种意义上使自己不再是自然之物。相较而言,库切的主人公K有着和西方传统迥异的自然观,他不再将自然视为意识反思之对象,也非崇高精神之唤起者,更不是自我成长的环境;相反,他的所有的斗争似乎都是为了被自然承认。这是一种承认的政治,它的核心是让人找到拥抱自然的方式:自然和人构成了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伦理关系——“我们”。 ①J.M.库切:《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邹海仑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年版,第页。本文以下凡引自本书的引文只在正文相应处注明页码,特此说明。 二、伦理转向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是一个重要的后殖民的伦理文本。后殖民写作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都不曾以伦理问题为中心,那个时期的作家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ibeichia.com/zbcjbxx/6993.html
- 上一篇文章: 楼视view走进鲍贝书屋,感受年前
- 下一篇文章: 桑枝的功效与作用,桑枝的食用禁忌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