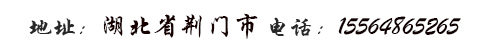四公十
|
北京哪个白癜风医院好 https://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 紫贝拾遗 原创文章,欢迎转发,谢绝转载! 作者丨静闻 图片丨网络图片搜索 在龙波牛市,四公一举成名。当地牛客争相宴请他,外地牛客主动和他交朋友,他们也都叫他“四哥”。 那一次,四公在龙波牛市买了十六头牛。这是他从两三百头牛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价钱并不高,如果将牛赶到琼山、文昌等地顺利卖掉,这一趟的收获是可观的。买到牛,四公准备再歇息一晚第二天早上就率队离开龙波。可当地的牛客却热情挽留他,说后天是关帝诞辰,龙波墟白天要举行盛大的庆典,晚上还要在关帝庙前演戏,时不可失,机不再来,错过了太可惜。牛客队的小伙子们也极力游说。四公知道这些兄弟跟他出来不只为挣钱养家糊口,更主要的是见见世面。牛客的生活本来就苦多乐少,如果他将行程安排得太紧,弟兄们那些本来就不多的乐趣会大打折扣,以后,还有谁愿意跟他出来呢?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暂且歇两天,跟龙波人一起过节吧。 关帝诞辰那一天,整个龙波墟都笼罩在快乐美好的氛围中,所有的商贩歇业一天,腾出干干净净的街道给关帝爷巡游。一大早,明媚的阳光才抹上龙波的街市,牛市附近的关帝庙就热闹了起来。人们身着节日的服装,喜气洋洋地从四面八方涌来参加庆典。一系列传统而庄严的祭拜仪式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关公在关平、周仓的护卫下乘轿出巡了。红漆雕花的大轿上,木雕的关公威武地坐着,由八个壮汉抬着走在最前面。他身着锦绣战袍,脚蹬白底黑金靴,左手握着宝剑,右手捋着三绺长髯,面若重枣,浓眉倒竖,一双丹凤眼不怒而威。关平、周仓木雕的脸板正严肃,他们一人手持青龙偃月刀,一人手捧帅印,威风凛凛地站在轿中,各由四个壮汉抬着跟在后面。抬轿的汉子一律着红装,显得隆重、喜庆。随着关帝爷出巡的还有当地人组织的鼓乐队、旗林队、舞狮队、装军队等,浩浩荡荡,气势非凡。观众成群结队地跟在巡游队伍两旁或后面,和关帝爷一起热热闹闹地出巡。 巡游队伍经过龙波墟市的大街小巷和邻近村庄,沿途信众焚香鸣炮恭迎帝君,祈求帝君护佑。在鼓乐队的吹吹打打中,旗林队清一色的壮小伙,每人手里举着一面“关”字大旗,昂首阔步向前走,大旗在风中猎猎作响,真有些古代将士出征的威风。舞狮队拿出浑身的解数,伏卧跳跃,把手中的假狮子舞得活灵活现,引得喝彩声不断。装军队走在最后,队中有在脖颈上戴纸枷或铁锁者,也有在臂膊上挂铁钩者,铁钩上还系着长链随地拖着走,长链在地上发出哗啦啦的声音,铁钩刺入肌肤经寸,装扮者竟若无其事。 最后,巡游队伍回到关帝庙,请出轿上的关公及其护卫关平、周仓,恭恭敬敬地端放在庙里的祭坛上,受信众们香火祭拜。鼓乐队、旗林队、舞狮队、装军队在关帝庙前来了一场大汇演,观者无数。 每一个热闹的节日都离不开吃吃喝喝,龙波人竭尽所能招待亲朋好友,街道上到处都飘着酒肉的香味。 这样的活动据说在琼岛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明代驻琼武官军士奉关公为军神,在关公诞辰之日扮关公游街,还在军中开展比赛活动,以此鼓舞士气,祈求战事顺利,并表明跟随武圣关公保家卫国的决心。后来传到民间,成为百姓祈求平安的节日。 四公长年在外闯荡,琼岛各地的习俗他大多见过或听过,这个关帝诞辰活动,他在别处也见过,只是时间略有不同,形式存有小异罢了。他给小伙子们放了一天假,由他们乐去,自己则在牛市旁的林子里守着十六头新买的牛,和一个来自定安的林姓牛客下象棋。 下象棋是四公在贩牛途中最喜爱的娱乐活动。他随身携带一副象棋,空闲下来,就摆开棋局,没有对手就自己跟自己下。下棋为四公旅途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还教会他学会思考。四公没上过几天学,他肚子里那点知识,大多是后来在社会中学的。这倒怪不了父母,是他自己无心向学。 小时候他和一群小伙伴在村里的祠堂读书,先生是村里一个老秀才,和四公同宗,辈份却比四公小。这个老秀才很是迂腐,往往用“宗积公”来称呼还是孩童的四公,这比小伙伴们的“暴牙公”还要让四公气恼。更加四公气恼的是老秀才的戒尺,黑盐木料,乌油油的,沉甸甸的,谁要是完成不了背诵任务,这戒尺就会火辣辣地落在谁的掌心中,四公最讨厌那些“之乎者也”,自然和黑盐戒尺亲近的次数也最多。每次挨打,四公都在心中发誓要烧了那把黑盐戒尺,却始终没有行动,因为他发现老秀才有几把同样的戒尺。烧不了戒尺,他就想办法干点小小的坏事报复老秀才。有一次,四公为了气老秀才故意爬上祠堂外的大榕树上撒尿,小伙伴们去报告老秀才,老秀才站在树下喊:“宗积公,快下来!”四公偏不下,还冲着老秀才装鬼脸,老秀才气得浑身发抖,声嘶力竭地指着树上的小长辈说:“我……我告诉你……你爹去!”因为老秀才的告状,四公经常挨老爹的责罚,再加上老秀才的课上得枯燥无味,四公在祠堂里勉强上完一年学,就再也不肯去了。 祠堂里的一年学习只让四公识了一些字,不至于当个“睁眼瞎”罢了,他的生存智慧全部来自生活这本大书。自从爱上象棋后,四公渐渐发现象棋就像一个高明的老师,常常带给他一些启迪。他在下棋中学会了全局思考问题,学会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学会危急时弃“车”保“帅”,遇到机会要像“车”一样果断利落……这些意外的收获让他更加喜爱下棋。 此刻,四公和定安的林牛客正摆开战局,横马跳卒,车攻炮轰,双方你来我往,小小的棋盘立刻热闹起来。这个林牛客长得膘肥体壮,紫红脸色,络腮胡子,说话做事显得很豪爽,颇像《水浒传》里的绿林好汉。他对输赢毫不在意,他的棋子在棋盘上横冲直撞,只图一时痛快,全然不顾后果。四公和林牛客恰恰相反,每一局都认真对待,每一步都深思熟虑,林牛客总是不耐烦地催促他:“老兄,又不是赌钱的,爽快些,爽快些嘛!”他笑呵呵地回应:“林兄莫急,莫急。”有时,四公思考的时间长了些,林牛客便急得直骂:“什么鸟人嘛?下个棋还要想这么久!” 四公却充耳不闻,继续凝神苦思,他总是将棋路想得远远的,直至胸有成竹了,才开始走子。他下棋的快乐就在这样的思考中。 四公连赢了几盘,林牛客觉得无趣,将棋子往四公面前一推:“什么鸟棋,还是喝酒痛快!”四公抚掌赞成,收起棋子,俩人开始饮酒、聊天。喝着聊着,话题不知不觉地往女人身上靠去。 林牛客呷了一口酒,那口酒从口腔进入喉咙,热乎乎地流进他的肠胃,酣畅传遍他的全身,他啧啧舌头,闭上眼睛陶醉般轻轻地“啊”了一声,又剥了几颗炒花生丢进嘴里,边嚼边看着四公嘿嘿地笑:“四哥,我看你也是为女人多留两天的吧?” 四公没有回答林牛客的话,只是端起酒杯饮了一口酒,一副不置可否的模样。多年的牛客生涯,他深知同行的德性,也理解同行的德性。男女之事,他总是随他们说去猜去,不承认也不否认,更不会解释些什么。 林牛客看四公不说话,以为是四公默认了:“老兄,你的那位相好的长得靓不靓?” 四公扬扬眉毛:“你说呢?” 林牛客拍拍四公的肩膀哈哈大笑:“按我说,我们这些牛客长年在外,能有个女人暖暖脚就是福气啦,哪能有那么多挑剔呢?不过,我的那位长得还真不赖!”林牛客说着又得意地呷了一口酒,接着告诉四公,他前日在龙波牛市上买了十头牛,已让跟随他的人赶回定安去了,他多留两天就是为了会会他的相好。 “兄弟,不瞒你说,我在每个牛市都有相好的。”他压低了声音眉飞色舞地说,得意的笑在喉咙处咕咕作响,“哈,处处无家处处家,家花不如野花香啊!” 四公竖了大拇指:“还是林兄厉害啊!” 林牛客更加得意起来,话越发说得糙了。 四公边饮酒边听林牛客吹牛皮,不觉得思绪已飘远去。 十八岁那年,随着海棠的离去,他的情感也枯萎了。没有了海棠的世界,所有的女人都是一相样的,他再也不可能像爱海棠一样去爱别的女人。王氏和他同命相怜,和他生儿育女,但他清楚王氏只是王氏,他无法对王氏产生一种狂热的依恋。王氏对他也是平淡的。不管他多久回一趟家,她永远不会抱怨;不管他在家停留的时间多么短暂,她也从不挽留。每次牛客队返乡,夜里和四公独处时,王氏从不问四公在外面的事,别的女人爱拐弯抹角地打探丈夫隐情的毛病,她没有,这让四公感到有点意外。想到在他离家的日子,她可能从未有过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思念或等待,四公心中就有了小小的失落。后来,他们有了孩子,孩子弥补了他们情感的缺陷,成了维系他们夫妻关系的活泼存在。 两个孩子对一年到头很少在家的父亲总是陌生的,每次四公返乡,王氏把孩子抱到他面前,不再像过去那样说:“回来了?”而是指指四公,对怀里的孩子说:“这是侬的阿爸,侬不是天天念着要阿爸吗?阿爸回来啦!”四公离家时,她也不再说:“要走了?”而是从四公手里抱过刚刚跟父亲混熟搂着父亲的脖子不肯松开的孩子,轻轻地安慰说:“侬不哭不哭,侬爸去市买糖糕回来给侬吃哦。” 四公在家时,喜欢带孩子们玩,却又不细心,孩子们笑着喊着跟他出去,回来时不是这个磕破皮了就是那个摔流血了。王氏从他手中接过哭得一塌糊涂的孩子,一边给拿毛巾给孩子擦脸,一边嗔怪:“看看侬爸,真会照顾阿侬啦!” 四公这时候总像犯了错事的小孩子,搔搔自己的后脑勺又捏捏孩子的小脸蛋,陪着笑说:“阿爸真笨,该骂该骂!”说着俯过头去,拉过孩子的小手去打自己的脸,孩子破涕而笑。 王氏也轻轻地笑了起来,她的笑是无声的。生了两个孩子后,她丰满了许多,刚嫁过来时略嫌清瘦的脸饱满起来,两片薄唇似乎也随着饱胀起来、红润起来。四公看着破涕而笑的孩子,眼睛的余光却偷偷地扫在王氏的脸上,他看到王氏总是紧抿的嘴唇微微地向上弯,两唇之间露出一弯洁白的弧线,就像天上的新月。四公知道王氏不是真的怪自己,心里竟涌起一股暖流。 的确,四公渐渐觉得王氏不再像过去那样冷漠得令人生厌,但不知怎的,他仍然无法对她产生一种热烈的情感,他总觉得他们之间隔着一堵无形的墙壁,他住在墙的这头,她住在墙的那头,见了面永远客客气气的。 这些年的牛客生涯,他认识了很多像林牛客那样的同行,同是男人,他理解他们,但他又不是他们。不是他比他们纯洁、高尚,而是没有女人能让他动心,就像十四岁那年在大姑家的小厨房里看到海棠时的那种怦然心动。 唯独那一年在长安牛市,他为一个女人小小地动了一下心。 那一次四公到长安牛市做买卖,女人的牛恰好犯病,经人介绍,她牵着病牛到牛市上找四公帮忙。四公一看牛骚动不安、张口伸舌流涎的模样,就知道牛犯的是常见的食道梗塞。他把牛头抬高,摸摸牛的食道,在食道靠近口腔的地方摸到了一个硬块,四公掰开牛嘴,拿两块木头卡在牛的上下齿间,将手伸进口腔,取出梗在食道里的硬块——那是一个地瓜——牛当即就好了。 女人非常欢喜,从口袋里摸出钱来要给四公,四公不收。要是一般人,道声谢就完了。这女人偏好强,不想欠四公人情,竟把钱塞到四公的口袋去。对四公来说,当牛客是他的职业,牛医纯属业余爱好,他从不收费。他从口袋里掏出钱来追上匆匆离开的女人,要塞回去。女人不让,钱被推来推去,就在那无意间,四公的手碰到了女人的胸脯,一阵温软的感觉顺着臂膀传遍他的全身,他被这感觉震得酥麻,手中的钱不觉得掉在地上。这一碰,两个人都尴尬了。四公结结巴巴地说:“钱,你拿……拿回吧。”女人的脸涨得通红,她匆匆弯腰捡起地上钱,拽着牛逃也似的离开了。 四公看着女人的背影,揉揉酥麻的手臂,心中竟溢起几丝欢快来。 那一天,他无法控制地一次又一次回忆起和那女人相处的短暂时光。从她惶恐不安地牵着病牛来到他面前,到她涨红了脸离开,他发现自己根本想不起那女人的模样,越是想不起就越要去想,最后只有温软的酥麻一遍又遍地袭击他的手臂,传遍他的全身。 第二天,女人又来了。她手里牵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子,用布包了十几个鸡蛋要送四公。这一下,四公看清了女人的模样。这是一个小巧的女人,身架子小,脸小,脸上的五官也小而精致。四公见惯了高个子的王氏,觉得这女人就像还没长大的小姑娘,但马上又觉得用小姑娘来形容她是不太正确的。小姑娘哪有她丰满的胸脯和滚圆的臀部?她的胸脯的确是太丰满了,把粗笨布衣的上部撑得圆鼓鼓的,随着她的行走、说话、呼吸,这圆鼓的胸脯就出现不同程度的起伏、荡漾,真让人担心那薄布衣会忽然暴裂开来。她的臀部比胸脯更丰满,肥大的粗土布长裤被撑得曲线分明,走起路来,臀部便有些颤悠悠的感觉。相比之下,女人的腰部则显得很纤柔,纤柔得惹人怜爱。 四公本不想收女人的鸡蛋,但又担心出现昨天令人难堪的推让,只好收下。但他同时又派了一个小伙子在墟市上买一些小孩子喜欢的零食和玩具,当他亲手把东西送给孩子的时候,孩子躲在母亲身后不敢接。女人叹口气说,孩子的父亲已经去世快两年了,没有父亲的孩子胆子小,尤其怕陌生的男人。她替孩子接过礼物,道过谢,就牵着孩子走了。 女人走后,四公解开布包,把鸡蛋一枚一枚地取出来放在一个竹筐里。放好鸡蛋后,他才注意到那块包鸡蛋的布,它不是常见的土布,也不是柔滑的丝绸,而是近年来在城里流行的洋布,蓝底上盛开着成簇的桃红的细花,细花上还勾着细细的白边,看起来很雅致。这是一块女人用的头巾,一块好料子的头巾。四公拿着头巾发愣:这个女人是什么意思?是想将头巾送给他,还是一时找不到包裹鸡蛋的材料才匆匆用了头巾?他有些作难,觉得把一块好端端的头巾就那么丢掉太可惜,而要还回去又有些难度——他既不知女人住在哪里,也担心让人看到了生出闲话。四公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把头巾叠好揣在口袋里,希望女人自己来取回头巾。 女人没有再来。四公在牛市上的买卖已结束,他要离开了。走前的那天傍晚,他在长安的墟市上信步闲逛,傍晚的墟市很宁静,长长的石板街上只有几个孩子在玩耍,低矮的瓦舍炊烟袅袅。四公看着玩耍的孩子,闻着空气里食物的香味,不由得想起自己的两个孩子来。此刻,他们在做什么呢?是屁颠屁颠地跟在母亲的身后,看母亲进进出出地忙活,还是缠着奶奶要糖吃?是跟着堂哥堂姐在院子里玩耍,还是拿着小棍追得小鸡到处跑? “牛客伯爹!”一个孩子稚声稚气地喊着,跑过来站在四公面前。 四公很快认出这孩子是那天女人手里牵的那个。也许是四公的玩具和零食收卖了孩子的心,也许是孩子得了母亲的教示,他称呼四公“牛客伯爹”。这个称呼让四公感到亲切,他蹲下来,抱起孩子,忍不住在那粉嘟嘟的脸上亲了一下。他记起口袋里的头巾,掏了出来,交给孩子,说,这是你娘的头巾,你拿去给她吧。孩子不接头巾,他从四公怀里滑下来,拉着四公往旁边的一间瓦舍走去,一边大声地喊:“娘,娘,牛客伯爹来了!” 四公刚被孩子拉进瓦舍的小院,那女人就出来了。她见了四公,嫣然一笑,眉眼间没有半点惊讶,好像她早约好四公在这个时刻到来似的。孩子见母亲出来接待客人,就跑出去继续和小伙伴们玩了。 女人仍是土布衫,胸脯也一如既往地高耸着,四公的眼睛不知往哪里看,他两只手揉搓着,难堪得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好半天才想起要把头巾还给女人。他把手中的头巾伸到女人面前,又不知要如何解释,只好为难地搔搔后脑勺,嘴里嗫嚅着:“你的,包鸡蛋太可惜了。” 女人笑笑接过头巾,请四公进屋喝口水,四公想婉言谢绝,腿脚却不听使唤地进了屋。 斜阳穿过院门将一抹暖光投进屋里,屋里显得很明亮。正中间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放着一个茶壶和几个茶杯,靠墙放着几张椅子,每一样东西都显得很洁净,在夕照的暖光中泛着柔柔的光。女人用四公还给她的头巾殷勤地拂拭过一张椅子的椅面,再请四公坐下,又给四公倒来一杯暖开水。 四公喝了几口水,和女人搭讪了几句,就感到心跳得很慌乱。他似乎有很多话要讲,却又不知讲什么才合适。女人倒比他冷静得多,她提着茶壶往他的杯子里续了水,说:“大哥啥时候离开长安?” “明天,明天。”四公忙不迭地说。 女人轻轻地“哦”了一声,就低头垂眸不再说话了。 眼见着又要陷入相对无言的尴尬中,四公忽然想起女人的牛,忙问:“你的牛还好吧?” “好着呢!我家小叔子借去拉货了。”女人顿了一下,有些伤感起来,“孩子的父亲过去也是拉货的。” “哦。” “小叔子每次用牛都会给我一些钱,牛算是租给他了。” “这样挺好挺好的。” “我小叔子建了新房子搬出去住了,他的孩子才几个月,婆婆也住在他家帮他看孩子呢。这个家就我们母子俩。” 女人说着就沉默了。 四公不知道女人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是寻常的闲聊还是有意在暗示些什么?他的心更加慌乱了,他感到浑身燥热,沉默了一会,他站起身来跟女人告辞。 女人也不挽留,在四公即将走出院舍的时候,女人好像记起了什么,突然喊了一声:“牛客大哥,等一等!” 四公的脚仿佛听到军令一般不动了。女人飞快地进了厨房,又很快从厨房里出来,手里多了一包东西。她把东西递给四公,四公不接,只是机械地问:“什么呀?” “豆腐。黑豆做的。”女人说,“刚做好的,正想给大哥送去呢。” 四公不去接,女人笑着拉起他的手把豆腐放到他手中。豆腐被一块干净的白土布包着,暖乎乎的,飘溢着特有的香味。 四公无心享受黑豆腐的香味,此刻,女人的手心正在布包下和他的手背亲密接触,那一只小手是那么温和绵软,一个手指头似乎还调皮地敲了敲他的手背,使得他原本慌乱的心一下子着了火,幸好女人笑笑拿开了她的手,不然,他真会失态的。 “干!”林牛客在半醉中举起了酒杯,“为我们的野花!” 四公也赶紧举起自己的酒杯,两个酒杯在空中脆脆地响了一声,“今晚九点……九点,嗯,约好的……”林牛客醉眼朦胧地说着,一头栽在酒桌上。 “干!”四公又朝林牛客竖起大拇指,一口将杯中的酒饮尽。 (未完待续)作者:静闻女,文昌人,生于乡野,长于乡野,热爱乡野生活,在乡野劳作至今。 征稿启事 《紫贝拾遗》证明了乡土文学是可以在民间自发地萌芽、生长、开花、结果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乡土文化的兴盛远远不是一时、一人、一地的事情。要形成一个有利于乡土文学成长的氛围,既需要大量的作者持之以恒地写作和讨论,也需要大量的读者持之以恒地阅读和批评。 我们欢迎所有作者继续给《紫贝拾遗》编辑团队投稿。所有来稿都会经过“一稿、二稿、定稿”这样一个严格的审稿、修改和校对流程。被《紫贝拾遗》编辑团队接受的文章,首先会通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ibeichia.com/zbcyxxg/5372.html
- 上一篇文章: 喝酒是个技术活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