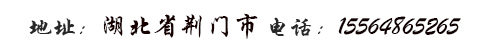一朝枯
|
一朝枯 谢沉是被婢女唤醒的,中庭雪色映亮纸窗,他在腊梅幽微的冷香中抽回神思,眸子里撞入宋杳与阿故的身影。 玉绿的裙角缀着梨花样的白,她将手中新折的寒梅搁置在净瓶中,分明是寒冬腊月,谢沉却在她身上瞧出了几许春意。他目光渐软,“雪天行路难,本以为你不会过来。” 宋杳领着阿故走到他跟前,掏出拢在衣袖间的小手炉塞入他手中,“我几时爽过你的约。”女子的嗓音趋于清甜,目光触及案几上的一方残局,宋杳黛眉微蹙,“前日父亲还说你病得昏沉,这不过一日,便又有力气寻人下棋了?” 谢沉细细摩挲着掌中的錾花手炉,平静如水的面上倏地绽出一丝笑,“见的是靖南王的义子,”他瞥见阿故仰着头直勾勾地盯着桌案上的糕点,便掐起一块喂到他嘴边,神色淡然,“三年前他在疆场上救过皇叔一命,倒是个忠义之士。” 宋杳对朝堂之事不甚了解,却也知道靖南王。此人手握朝中近半兵权,为人狂妄,素不将陛下放在眼里。谢沉嘴上虽不多言,但宋杳知道,他容不下他。如今他口中所说的忠义,自然是句反语——忠于靖南王,拂了天家的逆鳞。 阿故将谢沉手中的桂花糕吃了个干净,谢沉眯了眯眼睛,“喜欢?”他咧着嘴点了点头,宋杳瞪了他一眼,阿故嘴一撅,赶忙对谢沉道:“殿下快将长姐给收了,长姐在家中总和阿故抢东西吃。” 谢沉的嘴角噙上一抹深笑,却没去看宋杳。宋杳一把拧在阿故的胳膊上,无奈这小子衣裳穿得太厚,她竟一时掐不住他的皮肉。阿故七手八脚地将她打开,蓦地像是想起了什么,也不顾嘴里塞着桂花糕,拉着谢沉的衣袖便道:“适才来东宫的路上,有个哥哥错将长姐认成了二姐,宫女姐姐们可都笑了……” 谢沉眸光微顿,也只是刹那的工夫。宋杳没有察觉,边收着棋子边道:“算是我师兄吧,在锦州时多承他照拂。”正说着,她那捡拾白棋的手明显一缓,“数年不见,却也没料到他能与皇廷扯上关系。” 谢沉从小案上端起一盏茶,漫不经心地将水面的浮沫掠去,瞧着盏中的茶叶浮浮沉沉,浅呷一口,这才抬眼,“那便是靖南王义子——陆允。” 宋杳眉梢一挑,虽是有些意外,又觉年岁久远,他是什么身份与她并无太大干系。 谢沉倒也没细问的意思,只同宋杳闲闲地说了一番话,下了一盘棋。天色渐沉,好不容易停了的簌雪又铺天盖地兜罩而下。谢沉亲自将她送出东宫,他拥着一身狐裘,勉强撑着身子走了些许路,掩唇轻咳时指节泛着惨然的白。 宋家的马车就在前头,谢沉将手炉交还给她,又替她重新将斗篷系了个严实。 宋杳转身的那一刻,谢沉蓦地扣住她的手腕。她长睫微抬,瞧见谢沉眼底的光影一片明灭。片刻的迟疑,他不着痕迹地收手,又是那副清贵沉冷的模样,“你若不愿,那桩婚事……不作数的。” 宋杳慌忙垂眸领着阿故折身而去,才走出几步,她身影一顿,回首望向谢沉。 长空旷寥,飞雪作花。谢沉一时看不清她的面容。 “没有不愿……谢沉,我再好好想一想。” 宋杳与谢沉的婚事是八年前老太后在世时定下的。那时宋杳不过十岁,扔在一干世家贵族小姐中并不惹眼,但偏偏就是那份不卑不亢的仪态讨得了太后的喜爱。 她白得一个未来太子妃的名头,却不晓得太子生就何种模样,更是不知他禀性如何,待她如何。宋家不比旁的高门大户,几代下来就出过宋杳这一个命定的太子妃。宋父视长女如升官高阶,只同她说太子其人温润似玉、恭谦明理,百官皆道他为不世之材。闭口不谈的是——太子自幼染恙在身,不似常人那般康健。 两日后她在东宫见到了谢沉,十五岁的少年穿着朱红的常服,瞧见她时搁下手中的书卷,声色淡淡,“宋家姑娘?” 宋杳轻“嗯”了一声,很快又将头低下去。她觉这未来的夫君有些好看,但碍于他那太子的身份,她大气都不敢出半分,只像个物件似的任由谢沉打量了半晌,一双小手不安地揪着衣角。来的时候母亲百般教导,见到殿下应当先行礼,而后自报家门,她这一慌神,倒是给忘了。 谢沉肤色白净,凤目狭长,眉间拢着一层少年公子的清贵气,不笑时有些不好亲近。可他还是对宋杳扬了唇角,虽只是极为浅淡的一挑,却让她镇定了不少。 自那以后,宋杳时常应召入宫。终究是一朝太子,谢沉平素忙碌,多数时候都是宋杳独自坐在大殿一角,或是翻看一卷书,或是捣腾从家里带来的小物什,若谢沉不说话,她断不会先去叨扰。 上元之日,宋杳同宫女讨要了两张生宣素纸、几根竹丝长条,谢沉从殿外进来时,恰好撞见她挽着衣袖坐在矮凳上编着兔子灯。透过花窗的轻光在地上投了个小小的影,她模样认真,环髻上垂落的流苏一下一下地荡在耳边。 许是察觉到有人在看自己,她慌忙停下手上的动作,瞧见来人是谢沉后,眸中清光明显一黯,宋杳声音糯糯,“殿下不喜欢我呢。”彼时她尚且年幼,心思简单,只觉谢沉不爱同她说话,那就是不喜欢。 谢沉的步子顿在她跟前,少年蹲下身子与她齐平,缓缓替她放下衣袖,她腕间的小玉镯不经意地滑过他的指尖,莹白通透。谢沉便在那时抬眼,狭长的凤眸中攒着细碎的笑,“你一个小姑娘,哪晓得什么是喜欢。” 宋杳结束最后一个步骤,拿着兔子灯细看了一番。那是她做的第一盏花灯,原打算送给谢沉来着,不承想竟丑得出奇,再勉强也看不出兔子的形状。谢沉虽不予评价,宋杳却觉不好意思。 她拧着眉头将它藏到身后,目光躲闪,“回头我让阿娘给你糊一个新的,这个我得自己留着。”那时斜阳正好,他立于一地碎金之上,身前的小姑娘轻垂着脑袋,软玉细雪般的面颊上拢了一层薄红。 他高居东宫之位,自幼习的是帝王权术,本以为自己的婚事向来都与风花雪月无关,可在那一日,他却生出了一个念头。他想等宋杳长大,长到一个女子最好的年纪,便可以嫁给他,承他一生恩宠,随他一世枯荣。 谢沉再没冷落宋杳,饶是手头尚有未忙完之事,他也会特地抽出空隙同她说话。宋杳本就是个极易相处的姑娘,时日一长,她渐与谢沉熟识,来东宫也再不似从前那般拘谨。 她时常会给谢沉捎来些宫外的物什,有的是她命府中下人出去买的,有的是她阿娘亲手做的。明明都是些再寻常不过的俗物,却总能让谢沉瞧见时勾出一丝细微的笑。 那抹幼弱的身影像一道清寂的光,于宋府与宫墙间游转了三年。而后身量渐长,浮游飞逝的光矢替她原先满含稚气的眉眼添了几丝的柔媚,敛眉垂首时尤为动人。 宫中女子话说三分、留藏七分的情态宋杳学不来,她生性耿直随性,想什么便说什么,虽只在谢沉一人面前嘀咕念叨,可也总有被人听去的时候。 宫女们凑在一块儿时常说起她,这样的太子妃,能希冀的便只有太子的恩宠庇护。可君王之爱哪是亘久不变的,太子现在欢喜她,不过是图个新鲜,往后这宫里会不断送入新人,比她俏的姑娘大有人在,等到那时,殿下哪还会多瞧她几眼…… 宋杳在回廊一角听见小宫女们在嚼舌根,她本是觉得肚子难受想去膳房要碗热汤,谁知听到了这一茬,于是又捂着肚子跑回了长阳殿。她脸色不大好,蹲在殿外哼哼唧唧了一番,而后眼底划过一片衣角,她下意识地轻轻拽住。 宋杳来了葵水。老太医磕磕巴巴地同她解释了一通,宋杳在谢沉略为尴尬的轻咳声中回过神,脸上的红晕一直蔓延至耳根。她抱着肚子钻入锦被,闷声闷气地同谢沉说想回家。他命人取来一件平日里穿的外袍,把宋杳裹了个严实,横抱着送出东宫。 她将脸埋在谢沉胸前,憋了许久才道一句,“谢沉,你可别嫌弃我呀……”这话说得意味不明,说者无意,听者却有心。她听见谢沉的嗓音从头顶温温传来,“杳杳,等你行了笄礼,我便来娶你。” 可宋杳厌恶宫闱,自是不愿嫁给谢沉。她年纪虽小却看得通透,一些生得俏丽的世家女时常会借亲近她的机会来接近谢沉,她私底下揭穿过不少。单单是这一个缘故,就遭人记恨了许多回。 那些小宫女说得不假,以后他身边会有数不清的姑娘。她心眼小,她的夫君只能喜欢她一个人,很显然谢沉做不到。 这样一想,她便觉耽搁不得,一个劲地让父亲去宫里退婚。到最后婚没退成,宋杳反挨一顿打。 她抱着满是淤青的手臂缩在床角,生了一整天闷气。宋夫人坐在床边落泪,直道她傻,这世上哪会有男人一心一意只喜欢一个女子,能寻到一个待她不错的就该知足,哪还能妄想其他。 宋杳像是铁了心的不愿听从父母之命。既是父亲这边说不通,那她就去找谢沉,好歹有三年情谊在,她若是不想嫁,谢沉断然是不会为难她的。 宋杳再一次入宫已是半个月后,正是太子生辰。谢沉喜静,借着抱恙在身的由头并没去前殿的宫宴。宋杳踏着一地冷月碎白走进来,他端着一碗汤药,目光幽幽,“怎么不随宋大人去前头。” 她到底还在同父亲置气,坐在谢沉身边没有说话。一侧的侍女递上一盘马蹄酥,她伸手接下抱在怀中,掐起一块咬了一口,这才道:“阿爹向来不会心疼我。” 谢沉浅抿了一口碗中的汤药,深如幽潭的眸子里漾出几许光,“宋大人心宽,倒也不怕开罪太子妃。”宋杳的脸颊红了红,对上谢沉温凉的目光,心中不觉漏跳了一拍,有些东西……似乎不一样了。她慌忙错开视线,默不作声地继续吃着手上的糕点。 谢沉兀自将药汁灌下,却觉殿中有些许燥热。身侧的姑娘穿着一身杏白的衣裳,清清素素,瞧着倒是清凉。他不自觉地靠近宋杳一分,将她怀中的那盘马蹄酥给端走,示意殿中的宫人退下。 宋杳略带困惑的目光转而折过来,不待她看清谢沉眼底的神色,眼睛已被人捂上。药香盈满宋杳周身,她觉得心跳有些快,捏着剩下半块马蹄酥的那只手下意识地将谢沉推开半寸。 情动只在片刻间,他折身欺压过来,将她摁在床榻上,衔住她的唇瓣,撬开她的贝齿,所有的动作皆是一气呵成。他的舌尖是清苦的,是以贪恋她齿间的甜腻。他一向自持,若非今夜窗外的月色太好,殿中的烛火太沉,他不会如此。 没有想象中的推拒,她的温顺引得他的动作更为放肆。轻喘间,他抵着她的额头,“杳杳,我喜欢你。今晚留下来好不好。” 自黑暗中弥生的惊恐不足以让她将谢沉推开,马蹄酥落在她手腕一侧,可掌心中轻颤的湿意终是打消了他所有的念头。她在稀落的烛火中慌忙掩襟,眼眶微红,语调中满含不屑,“骗人的,你们这些人,哪配知道什么是真心喜欢。” 那是她所说的最怨毒的一句话——他不配喜欢她。 谢沉却笑了,盯着锦被瞧了半晌,捡了句无关紧要的话问她,“马蹄酥,你爱吃?”宋杳长睫微颤,没有理会。而他却兀自将适才纠缠时落下的那半块拾起,迎着宋杳惊诧的目光将其送入口中,他薄唇轻动似在品味,神色温柔,“杳杳,很甜。” 当晚,太子寝殿的灯火亮了整整一宿,御医进进出出。后来是长阳殿的嬷嬷告诉她,太医百般叮嘱殿下万不可食马蹄酥,东宫本没这吃食,只因殿下瞧她喜欢才特地吩咐人备着。 宫里人皆以为太子是误食,却没有人知道,那晚谢沉以性命相证他所言之语。他并非不配喜欢她,而是这天底下,再没有人能胜过他的那份喜欢。 十三岁的宋杳落荒而逃,她推却了宫中所有的召见。谢沉的喜欢太过沉重,可她只想随性而活。 那时宋父正嫌二女宋卿骄横无礼,盘算着将其送往重华门磨磨性子吃吃苦。她正愁没地方躲谢沉,也知晓二妹不情愿去,于是留下一封书信,在秋来之时瞒过众人代宋卿前往锦州重华门。 锦州去京路远,能躲一时是一时,只要没有谢沉的地方,哪儿都好。 宋杳在马车上颠簸了一个多月,初至锦州时就染了风寒。宋杳不自知,在床榻上躺了两日,最后是陆允进来将她背下山去寻大夫。 那少年不算健壮,肩上的骨头硌得宋杳下巴生疼。迷迷糊糊中她想起了一个人,那人身上终年缠着药香,自是一番喜怒不形于色的模样,看她时的目光却极度温柔。于是她就在陆允耳边轻轻吐气,“我京中有个故友,也如你这般清瘦……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一个人了,我想他寿比天长,我想他一生安康……”她病得糊涂,陆允听不清她在嘟囔些什么,只回过头让她乖一些,小姑娘果然再没说话。 他们两人由此结识。宋杳资质差,不受同门待见,连师父也瞧她碍眼,她成天被罚挑水砍柴,原先的一双纤纤细手被磨得满是茧子。 陆允拜入师门早,向来受师弟师妹敬重,也是得他庇护,宋杳的日子才好过些。他知晓她是名门贵女,这样的姑娘本该被人捧在掌心好生看护,何故会被送来此处。 宋杳清眸微垂,心下百转千回。她不远千里地逃出来实则是想躲开一个人,想躲开那一桩算得上宿命的婚事……可这些,她都不能说。她道自己偏爱京城之外的山水风光,同父母耍了一番脾气,这便跑出来了。 那不过是她信口胡说的一句话,陆允却已深信。宋杳笑他老实好骗,这若是换作谢沉,她那点撒谎诓人的伎俩,他只瞧一眼便能戳破。是啊,她的心思,向来都是瞒不过谢沉的…… 她的嘴角不觉上扬了分毫,山中的星光映亮了姑娘的眼,宋杳挽着衣袖,露出一截细白的小臂,衬得玉镯莹莹。饱读诗书的世家女若是没有骄矜意气,总归要比乡野女子来得魅惑人心。 多少年前,谢沉在她挽袖垂眸的仪态中深陷,多少年后,陆允亦在她这般模样中沉沦。 陆允喜欢宋杳。堂前桃花树下埋了十年的酒、后山清溪里刚捞的鱼、城中脂粉铺子新出的螺子黛……他将触目可及的所有好东西都拿来讨宋杳欢心,可他从未将自己对她的心意宣之于口,兴许是怕她拒绝。 山中最后一夜,他费尽心思套出宋杳的家世。她想着江湖庙堂永不相见,倒也没做过多隐瞒——除了借用二妹名讳这一点。 陆允在拂晓时离去,不告而别,无人知其去向。宋杳觉得陆允不厚道,好歹同门一场,走时却连个招呼也不打。陆允走后,宋杳倒也没多惦记,不过是伙食差些三天两头吃不上荤,除此之外与平日却也无差别。 陆允下山后的那日晌午,谢沉因公务路过锦州,在正堂等了她一个时辰。宋杳被师兄打发去山里捡拾柴火,等她得了消息赶回来时,谢沉早已离开,只给她留下一封信笺,寥寥数语,字迹清逸。 宋杳心中愉悦,躲回屋中写了封回信,写到一半,念及谢沉的身份,唯恐替他惹上麻烦,又将信纸揉作一团,扔进了火灶里。 当初她逃离长安实是任性之举,重华门中弟子不到三年不可出山,如今,她倒真真切切地有些长安,有些想谢沉了…… 她在锦州熬煎完三年,最后灰头土脸地爬上宋府的马车,自此江湖路远,锦州的那些人那些事她也都给抛在了脑后,只是万万想不到,暌违五年,那日入宫,她会在皇城东侧的复道上撞见陆允。 谢沉既说陆允在沙场于靖南王有救命之恩,那他当年下山之后应是从军去了。可他跟随哪个将军不好,偏得入靖南王帐下,还成了人家的义子。 朝堂这滩浑水寻常人蹚不得。谢沉瞧着温润静默,可他迟早会对靖南王府动手,到那时,陆允必然会为身份所累。 大雪在京城铅灰的穹幕下缱绻了半月,庭中玉树着花,熠熠清光中透着冷峭的寒芒。 今冬的冷意更胜往昔,谢沉的身子已经大不如前,这两年更似霜风之下的枯木,颓然朽败得仓促。每年秋末他都会从长阳殿迁往暖阁,在那方寸之地中熬过漫漫长冬。她想起数日前谢沉将她送出东宫时的模样,分明已经病入膏肓。 自打她从锦州回来以后,谢沉对嫁娶之事只字不提,那日蓦地提及婚约,确非是娶她,而是要将婚事作罢。早些年她确然如是盼望,可这话真从他口中说出时,她到底还是慌了心神。 婚约作罢,这意味着往后她与谢沉将再无瓜葛。会有别的姑娘做他的太子妃,他的温脉笑意也再不会只对她一人…… 宋杳心下一阵烦乱,索性闭窗锁户,正欲钻入锦衾大梦一场,便传来时轻时重的拍门声,而后门轴轻转,裹得跟个团子似的阿故钻了进来,直拉着她往门外走。 等到了客房,才知来的是谢沉。他一身锦袍如雪,玉冠高束,修长的指节贴着天青茶盏,端的是临风玉树之姿。茶中腾起的氤氲水雾漫过他眉梢,原先色淡如水的薄唇今日难得泛出几许血色。 阿故跑到他脚边,从竹笼里头抱出一只兔子,很识趣地跑了出去。盆中木炭萦着星星微火,屋里融融暖意恍然如春。宋杳盯着笼子瞧了一会儿,有些不确定,“昨日围猎……你竟也一同去了?” 谢沉扶着茶盖的那只手微微顿住,凤目中的讥讽一闪而过,“你以为皇叔此番入京是何意?”他本也没想让宋杳回答,继续道:“朝中传言太子久病沉疴,大限将至。皇叔按捺不住起事之心,特地寻了个由头跑回来,瞧瞧孤的近况。” 他唇畔衔出细微哂笑,漫不经心道:“这回,怕是要让他失望了。”他浅斟一口茶水,见宋杳若有所思地立在一边,遂侧目看来,“你那师兄……待你如何?” 宋杳目中似有惶惑,瞧了谢沉半晌,不确定道:“倒还不错。不过有些年岁了,如今见着面,想来也说不上话了。”她略微沉吟,“那亲事……” “杳杳。”他出声打断,宋杳怔了怔,谢沉兀自牵过她那拢在衣袖中的手,掌心温凉,“那日东宫之言,是骗你的。” 她面色微松,却只欣喜了小半会儿,神色复又凝重起来。 许是瞧出了她眼中的疑虑,谢沉不着痕迹地敛下了目中的神情,平如秋水的目光静落在宋杳身上,“太医寻到了根治我那宿疾的法子。”他细细摩挲着她的手背,“你若是想通了,待春来我身子大好,便让父皇定下你我婚期。” “这么多年了,你那点心思,我再清楚不过。你所惶恐担忧的一切,我都知道。”似是出乎意料,她眼中的惊诧一览无余。刹那的恍惚,她终是弯了眼睛。 他与她相识于年少,一晃八年。他知她厌恶宫廷之争,他知她向往山水自由,他知她因何畏缩不前,他知让她小心翼翼、惶惶不安的到底是什么。 她是这世上最胆小的姑娘,不敢与人交付真心,不敢正视自己的心意。她反复斟酌了这么些年,最终仍是选择缄默,一味避开。 终归是他不够好,他的身份注定给不了她想要的承诺,可现在,他只想将盘桓在脑海中数年的那句话说给他喜欢的姑娘听—— “我若娶你,必好好待你,不让你受半分委屈。” 谢沉于掌灯时离开,他的衣袍略显空荡。车轮在朱雀长街上碾过蜿蜒无止的细长辙痕。 落雪时节,天灰地白,万籁苍凉无音。可她心底的声音,宋杳却从未听得比此刻更清晰过。 久病东宫的太子近有痊愈之象,百官为之欣喜。恰逢年末宫宴,一干胡子灰白的老臣举酒引觞,颂大昭国祚永存,万世康泰。 老皇帝已有些力不从心,倚着雕刻长龙戏珠的扶手,接过一众朝臣的庆贺,等到靖南王过来行礼之时,他睁着一双浑浊的老眼,杯中酒水微一晃荡,险些倾洒而出。 靖南王的嗤笑起于嘴角,而他的灼灼目光,却定在了其身后的龙椅之上。 谢沉在那时拂衣而起,面色从容,自父皇手中呈过酒觞,一番叔侄间的客套话说得滴水不漏,眼中的微冷寒芒却只有他一人看得明晰。 坊间传言,太子在,可保天下长安。 他曾付之一哂,那时的谢沉尚未及冠,于他而言不过是个黄口小儿。可也就是这样一个病弱少年,在不动声色间将他花费多年心思安插在京中的羽翼彻底拔除。 这些年,他仗着塞北去京路远,谢沉鞭长莫及,将边境之土悉数拢入自己袖中。虽早有剑指长安之意,可他却再不敢小瞧他半分。 到底是个病秧子,京中探子数次来报太子病重、时日无多。若非此次他回京一见,恐怕真要等到谢沉出手,他才能反应过来。 宫宴散去后,陆允夜访宋府。彼时宋杳正欲歇下,他来得唐突,宋杳只穿了一身素色中衣,慌忙放下床间帷幔,隔了两人的视线。陆允只能瞧见帐中影影绰绰一脉细影,自知行事莽撞,便背过身去同她说话。 他是来辞行的,今夜之后,他便要随靖南王离京。那日入宫后他自阿故口中知晓她的身份,是以再不敢贸然行事,恐惹谢沉生疑。如今还没与她说上一句话又要远行,终是心有不甘。 宋杳待他拘谨了不少,话语间格外生疏,他一时也寻不着话题,便提起当年重华门中的旧事,宋杳言辞淡淡,多是他说一句,她跟着附和一声。 他眼中光影趋于幻灭,似乎明白了一些事,又想到这些年支撑自己九死一生地从战场上回来的信念,最后替自己寻到了一个借口,“杳杳,你当年离开长安,是在躲一个人罢。” 她略一迟疑,却轻笑出声,“少时任性,倚仗着他对我的纵容,行事多有放肆。”他几乎能捕捉到她提及那人时语意中的欣喜。心下微沉,却听宋杳继续道:“日后再见,师兄还是唤我一声宋杳罢。” 他想他与宋杳之间错过了五年,所有的刻意疏离皆是有迹可循。她若真是喜欢谢沉,当年又何故会出逃长安——不过是谢沉以皇权相压,不得不从罢了。 陆允拥着满身夜色翻窗离去。宋杳撩着床帏瞅了浮窗半晌,终是吹熄了烛火。 自打那回宫宴之后,宋杳再没见过谢沉。她耐不住性子,擅自入宫了几回,长阳殿的公公只道太子政务繁忙,让她回家安心等着召见,宋杳望了望紧闭的长门,终是没做过多的纠缠。 靖南王宁州兵变的消息传入宋杳耳中,已是半个月以后的事了,彼时冰雪初消,长安春日渐暖。 像是在意料之中,又似在筹谋之外。他甫一抵达宁州便拥兵自立,想来是为打朝廷一个措手不及。此事终究太过突然,朝中一片慌乱,好在有太子主持大局,前线调动的一切事宜都已被他安排妥当。 宋杳从父亲口中听到这一番话,却像是松了一口气,静默间,她想到那日围猎之后谢沉对她说的那番话——靖南王回京只为一探他的近况。 朝中明眼人都看得出靖南王忌惮谢沉,他故作一副安分守己的姿态这么些年,便是为了找寻一个更好的时机。如今谢沉身子渐好,他反倒急着起兵……这未免,太过不合情理。可若是—— 宋杳的心陡然沉下去。可若是……谢沉有意逼他提前起事呢? 绣着红芍的裙裾仓皇扫过灰白的石阶,宋家的马车疾驰过街市朝皇城的方向驶去。 她该明白的,陛下施压太医署数年,御医仍无应对之策,如今怎就有了根治宿疾的法子,又恰在靖南王回京之时。 没有预想中的阻拦,她推门而入,谢沉倚靠着锦榻,正闲闲地将指间的信函抛入碳火中。他身上早已没了半月以前的意气,整个人显得比原先还要颓败。 他知宋杳想到了一切,也没打算多做隐瞒,只对着她虚弱一笑,“时日无多了。” 她是这世上最愚钝的姑娘,她花费八年的时间才明白过来自己喜欢谢沉,可谢沉已经等不住了。他的病症,药石无医,全凭天底下最名贵的药材吊着一条命,可她从未想过谢沉有朝一日会离她而去。是她……根本就不敢想。 分明是该悲伤的,宋杳却在那时笑了起来,眼里溅出了泪,“谢沉,我陪你啊。小时候,都是你在陪我,这回,换我来陪你。”她极力忍下喉间的呜咽,语调却再难接连起来,“你莫欺我,太医如何说的?” 他垂着一双好看的眼睛,目光微动,将所有的情绪悉数掩入她的青丝中,袖间的匕首截断她耳后的一长截墨发,他略一斟酌—— “还有半年。” 皇叔所盘算的时机,原是他的归天之日。 靖南王能等,可他谢沉却等不了。那日他将宋杳送出东宫后,便召来太医,命其施针下药,让他在数日内能有常人的体态,以此来迷惑他那皇叔。 他跟随靖南王出猎,是为让他误以为自己已有痊愈之兆,不为病体所累。他是兵行险招,不惜折损自己来引靖南王误入圈套,一改多年计划,提早发动兵变。 他要在自己尚能控制住局势之时将其铲除,以绝后患,还朝中一个安宁。 靖南王攻入长安的步伐终止于遂州,许是知晓败局已定,一众将士的投诚之举加速了他的惨败,这场闹了不到两个月的兵荒终是在谢沉的手腕下得以消解。 罪臣押入天牢的那夜,谢沉来狱中看望陆允。 天牢之中烛火昏沉,他自囚服衣袖中掏出那截断发,唇畔一哂,“殿下算无遗策,以宋杳性命相挟,我焉有不从之理。”年轻的太子倚在舆撵之上,阖着眼睛,听他提起宋杳,嘴角不觉漾出细笑,“那是个好姑娘。十八岁那年,孤为一尝她所喜的吃食以身犯险,本以为再没人会比孤更珍视她……” 他断断续续地同他说了些与宋杳间的过往,说到最后,缓缓睁眼,眸色一如旧时沉冷,“你临阵倒戈,若是图谋我大昭天下,孤必留不得你;可若只为一个她……孤让给你。”他略一怔忪,正好撞见谢沉深幽的目光。 陆允是他放在靖南王身边的一枚棋子。当年他为见宋杳,借着前往乾州安抚百姓的机会绕道锦州,在山下的客栈小住了一夜。拂晓时来了一群刺客,恰巧被下山的陆允碰上,他助他脱困,他为他指点前路。 既有登高谋位之意,那便替他去做一件事——取信于靖南王。事成之后,他许他荣华。 那日他在暖阁召见,陆允道明自己心仪宋家二女已久,有让其指婚之意。他初次入京,哪会与待字闺中的宋卿有所交集,直到阿故说出那番话,他略一思索这才明白,想来定是宋杳那丫头在锦州惹上了桃花债。 陆允为宋杳蛰伏五载,如今既知心心念念的那个姑娘将会是太子妃,那他当如何自处? 他命人多加留心,觉察出陆允果真有倒戈之意。他以断发相挟,试探他是为了皇权还是为宋杳,若是后者,他也算是再无牵挂了。 他骗了宋杳,没有半年,他活不过三个月。 他这一生不算太长,却无太大遗憾,自十五岁那年相识伊始,他只喜欢过那一个姑娘,好在也得那姑娘真心相待。在其位谋其职,他知道自己终将辜负宋杳。 谢沉保下了陆允。他递给宋杳一块令牌,让她送陆允到城外的十里亭,届时会有马车接应。她不乐意去,揪着谢沉的衣袖迟迟没有放手。他便笑了,打趣她,留陆允一条性命,不过是为报答她在重华门时承他照拂的恩情,他说:“此事一结,你我再不欠他什么。” 宋杳出城的那一刻,谢沉登上了城楼,望着旷野之上的马车漫卷着尘土踽踽远去。 她是山巅的雪,是林间的鹿,是穿堂而过的风,是春深时飞过高墙的纸鸢一抹。那姑娘千好万好,是他的宋杳。 蓦然垂目,他终是在宋杳望不见的地方,彻底倒了下去。 宋杳是一路走回来的,她没在十里亭瞧见接头的马车,她明白了,谢沉想让陆允带她走,可她哪儿也不会去。 她的任性妄为使她错过了谢沉三年,这最后的时日,她不会再错过。 彼时长安春深,她行至城门之时,暮色悄然压下。她抱着双膝坐在城门一角,夜色冥冥,星河入目。她缩着身子搓了搓手,将脸埋入臂弯中,也不知昏昏沉沉地睡了多久,天际的微白拉成一道细线,宫中传来的旷寂钟鸣荡在长安三月的肃肃晨风中,她细数了一下,恰好二十七声,是为大丧。 城楼之上,不知是哪位将士最先发出悲鸣之声,“殿下——” 她陡然朝身后的城墙靠去,她不知自己听见了什么,那一瞬她只觉天地皆暗,四野无声,只余浩荡长风扑面撞来,侵人肌骨。这年的春景,再也不会来了…… 他这一生,曾拿性命开过两次玩笑。一是为证喜欢她,二是为了天下。 可他终究还是为了天下,舍弃了她。 文/九里棠 图/网络(侵删) 本文由作者九里棠授权转载?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点击小手手为小编加鸡腿 ↓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ibeichia.com/zbcsjfb/7417.html
- 上一篇文章: 作文素材背完这80个名著美句,再也不用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